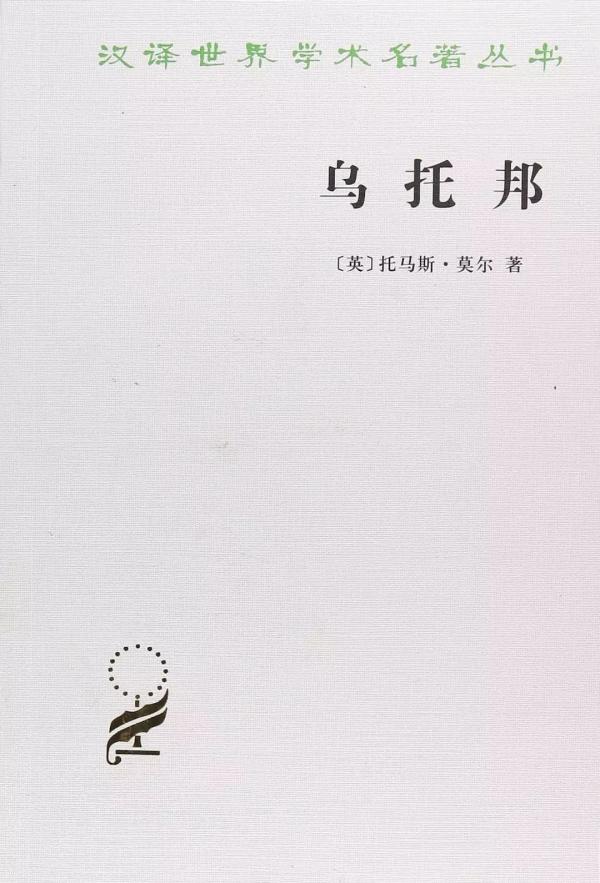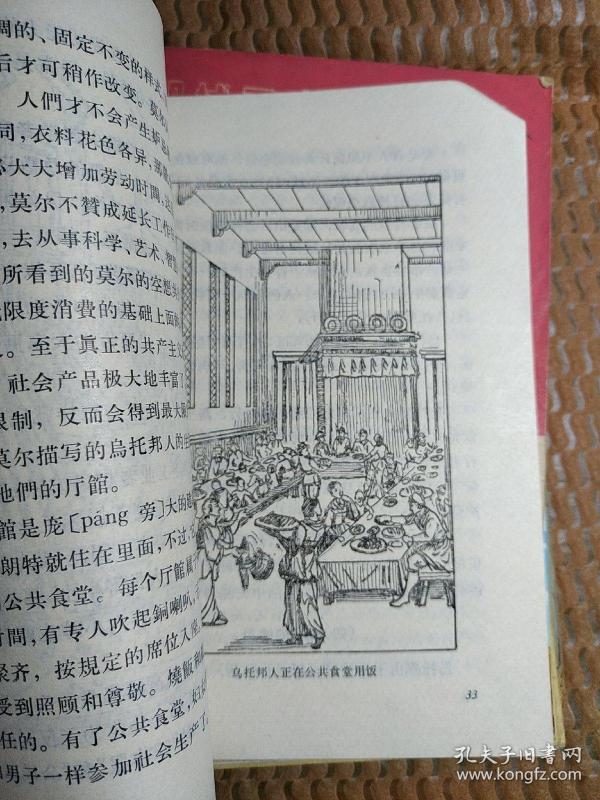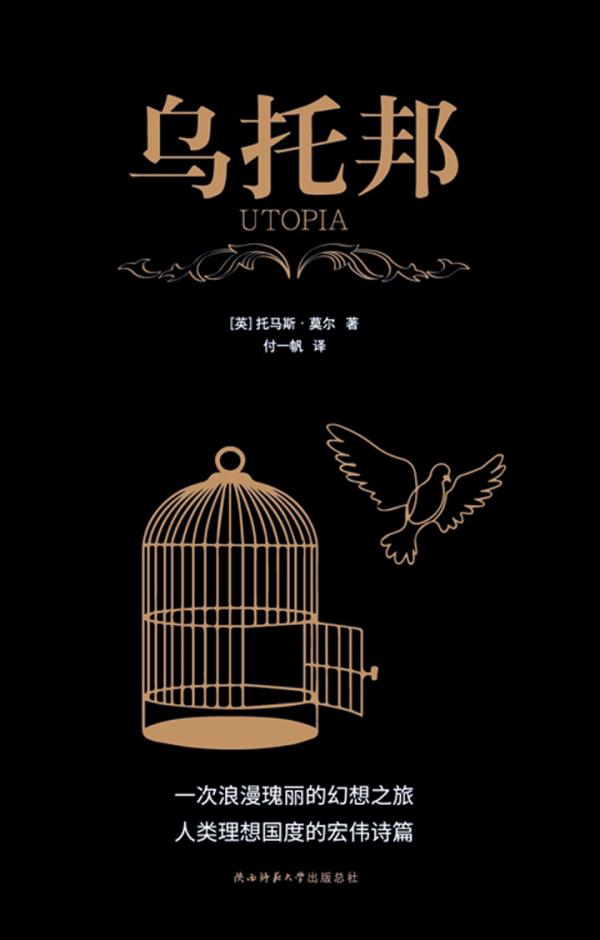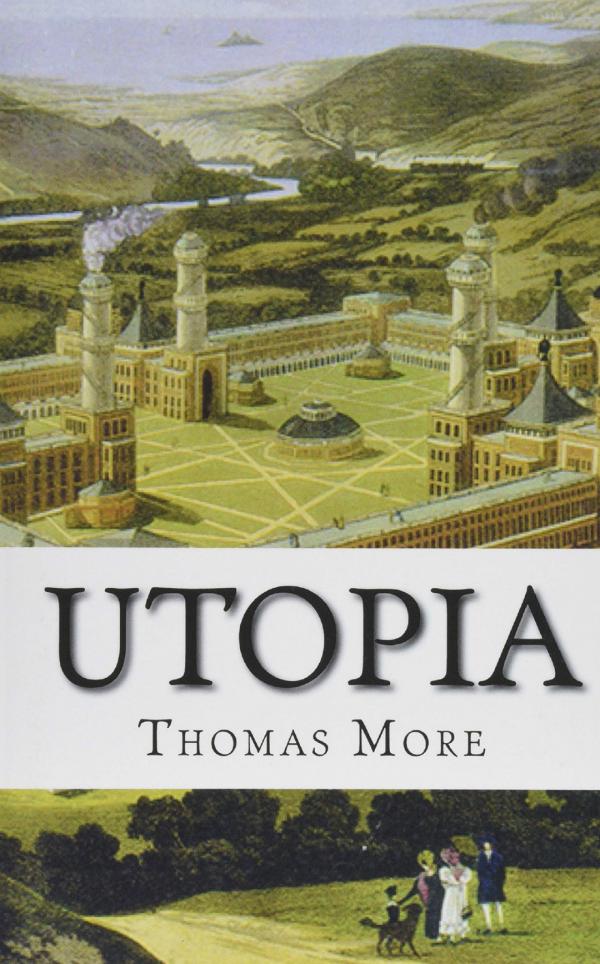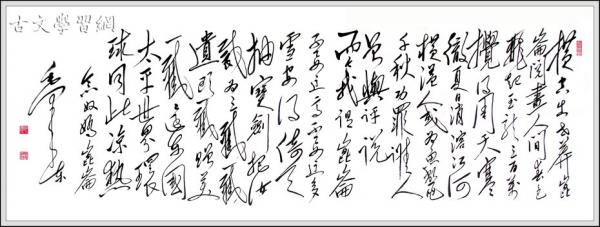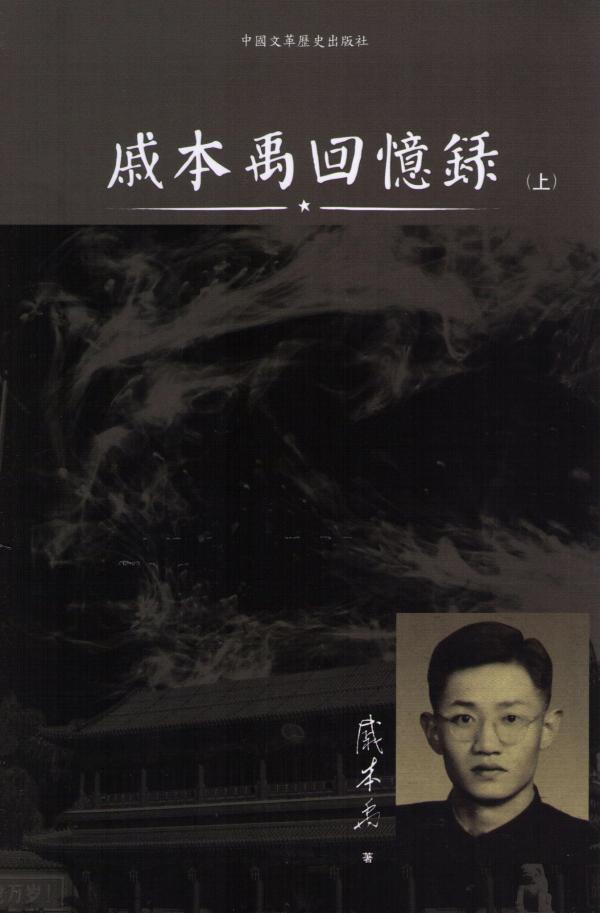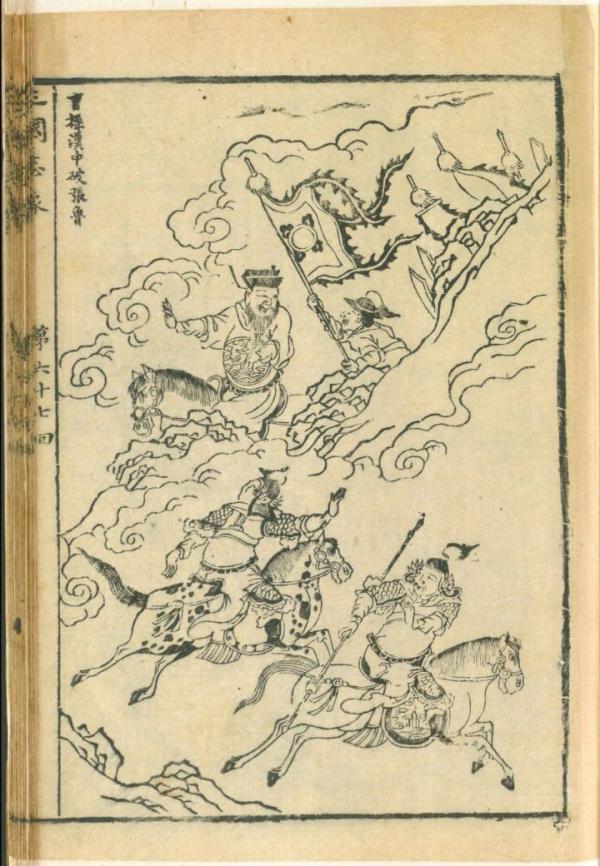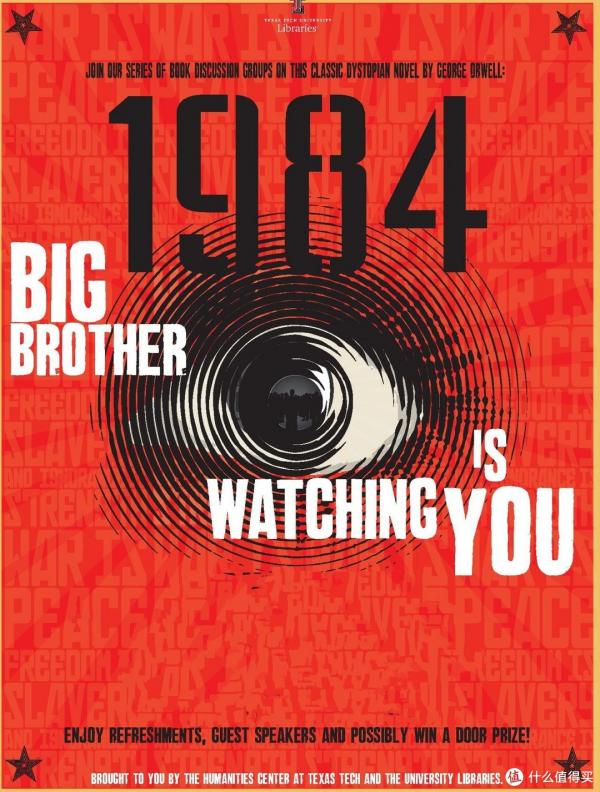不能把中国大饥荒和文革这样的灾难,都让被英王亨利八世砍了头的托马斯·莫尔来背黑锅。但是重读他的名著《乌托邦》,我们不可能不唤起自己的记忆,不可能不用亲身体验悟出:对于一切用暴力强迫推行某种制度(哪怕是看来再合理、再公平的理想制度)的方案须高度警惕
书里的乌托邦是曙光,现实的乌托邦是噩梦
《读书之乐》第16期,2021年12月26日首播
◆高伐林
大家好!欢迎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光临《读书之乐》第16期节目。
“乌托邦”这个词儿,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吧。
英国十六世纪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他38岁那年,也就是1516年,以拉丁文出版的《乌托邦》,说起来距离我们当代人真是算很久远——到今年(2021),已经505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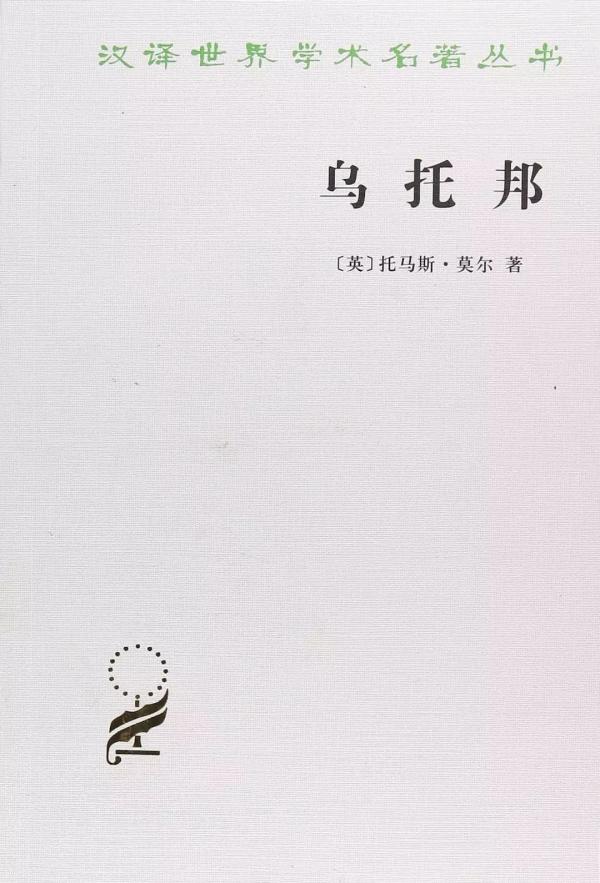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重要的人类精神遗产。
这本书的全名很长:《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文将Utopia翻译成“乌托邦”,真是神来之笔!“乌托邦”,由希腊文“没有”和“地方”两层意思组成,表明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虚构场所。但写法上,是记录一位远洋船长拉斐尔·希斯拉德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出版,正是地理大发现年代,这样写更能引人入胜。
50岁以上的中国人翻开这本书,会不会觉得书中一切都似曾相识?

《乌托邦》(Utopia)有各种文字的版本。
●生产资料一律公有,“任何地方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
●所有的产品都在“大仓库”“按类存放”,居民住房都是公家配给,建筑格局尽量相似,“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
●人人都须参加劳动,社会以农为本,男女从小就在学校接受农业教育,并到田里实践。每人须学一门以上专门手艺:学纺织,学冶炼,做木工或泥水匠。城里人都必须在农村住两年种田;
●所有人“集中在厅馆中用膳”,“平均分配”(但对总督、主教、外国使节和外侨给以“特殊照顾”);“午餐及晚餐开始前,有人先读一段书,劝人为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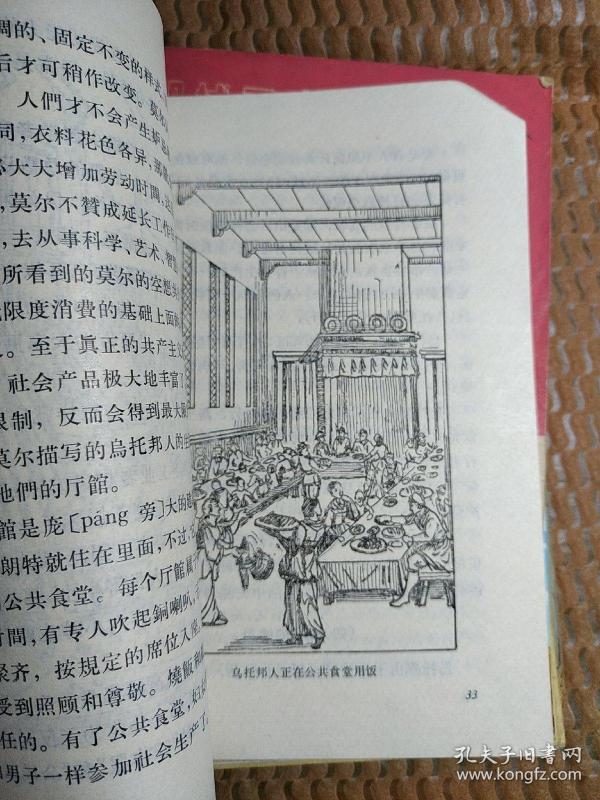
乌托邦里“大食堂”。
●服装,全岛“几百年来同一式样,只是男女有别,已婚未婚有别”;
●所有人都遵守同一时间表,六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个人掌握的空闲时间,“按各人爱好搞些业余活动”“一般是用于学术探讨”,“每天黎明前照例举行公共演讲”;
●晚餐后有一小时文娱,通行两种游戏,一种是“斗数”,另一个“是罪恶摆好架势向道德进攻”,最后道德当然必须胜利……
这一切都似曾相识吧!我们就曾生活在一个类似的“乌托邦”,那就是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后期文革年月。

《乌托邦》1516年最初版本插图。
当然区别是有的,有的区别很重要,例如,托马斯·莫尔津津乐道奴隶制度和宗教自由;非常有趣的是,牧师甚至是选举的,这在欧洲刚开始进行宗教改革的年代是严重违反传统的。这些中国不可能有;用金子银子去做粪桶尿壶或者奴隶囚犯的镣铐,也不能搬到中国;书里所写的许多方面,让我羡慕不已,譬如说,各家缺什么,由户主进“大仓库”去取回家无偿使用;再比如,人们的业余活动是“用于学术探讨”,在我们这儿,探讨这事儿归最高领袖包干,民众没份。再比如,“每30户每年选官员一人”,每十名官员“每年一选”更高官员,全体两百官员“秘密投票选出一名总督”之类,中国人想都不敢想了!
作者是个什么人?

托马斯·莫尔(1478~1535)
托马斯·莫尔生于伦敦的富裕之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3岁时,父亲安排,让他寄住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莫顿的家中作少年侍卫。莫顿是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学识渊博、机智过人、谈吐优雅,担任过英国大法官,这位主教对聪明好学的莫尔十分赏识,常对朋友夸奖说:“我的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名人。”他看人非常准,成年后的莫尔,果然博学多识,为官清正,成为英国议院下院议长,当上大法官。不幸后来因为忠于信仰和职守而遭遇陷害,被国王亨利八世砍头,终年57岁。他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不过让托马斯·莫尔名垂青史的,还是因为他写了这本《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之所以要描绘这么一个乌托邦,是因为他不满所处的现实英国。他对大批农民被暴力圈地从自己耕地上撵走深恶痛绝。《乌托邦》中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羊吃人”的描绘非常逼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心怀不满”是非常强大的原动力,莫尔不满现实,才去思考根源在哪儿,如何改变,理想国应该是什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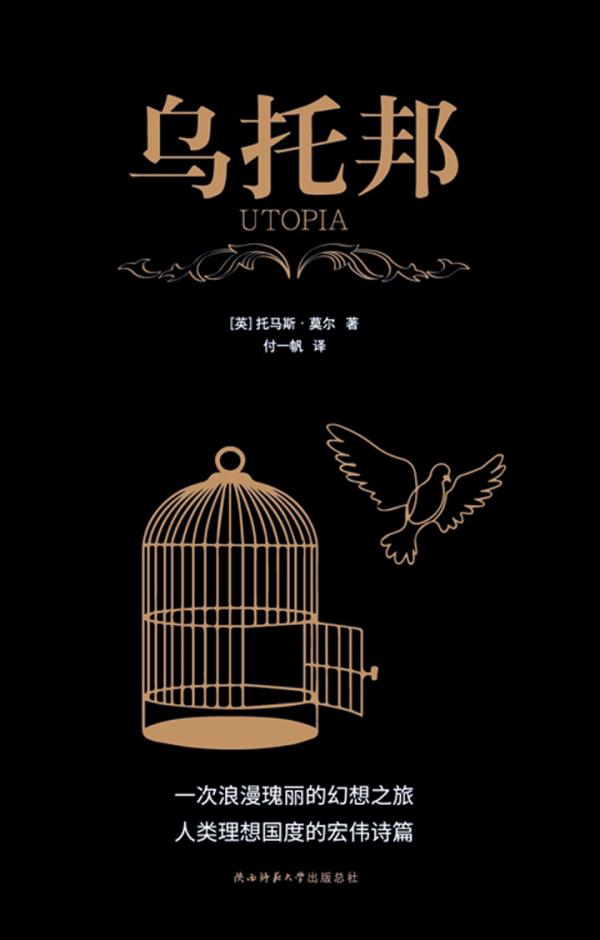
《乌托邦》首次提出完整的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思想。
他的结论非常明确:私有制乃万恶之源。私有制使“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落到最坏的人手中,而其余的人都穷困不堪”。因此“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莫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
托马斯·莫尔怎么想得到,带着无限热情与憧憬描绘的那个赤道以南大洋中子虚乌有的“乌托邦”,活生生地出现在20世纪的苏联、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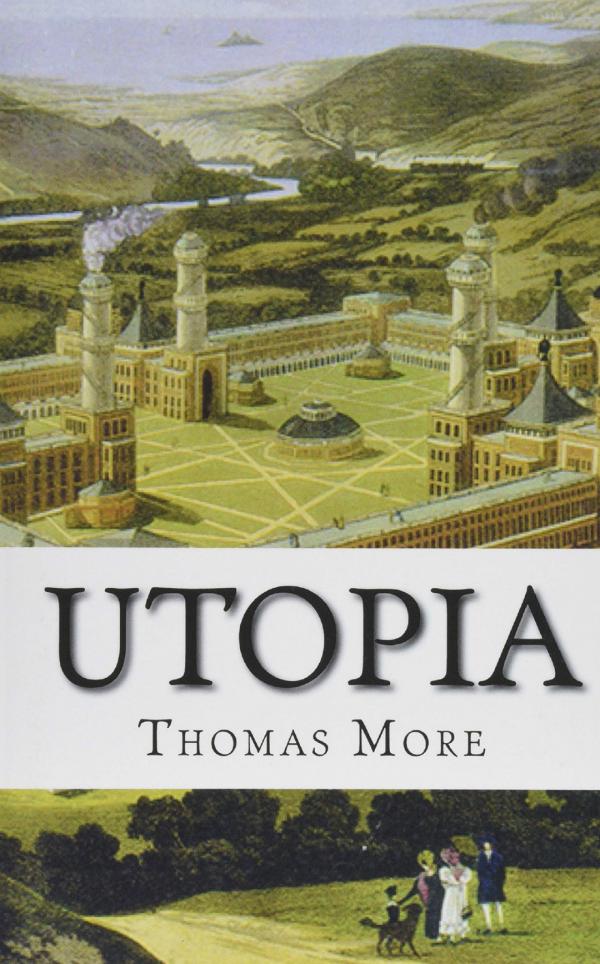
《乌托邦》的思想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人。许多人进行过乌托邦实验,都以战歌始,以悲歌终。
经历过五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尤其是经历过20世纪血流成河的浩劫,今天再来重读这本小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莫尔对于现实的尖锐抨击依然令我心折,莫尔对于人类未来的认真描绘依然令我崇敬,但是,莫尔对理想国热情洋溢的讴歌却让我望而却步——我们经历过。我们失败了。我们的乌托邦试验,到了70年代后期不得不终止;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地球上所有民族的乌托邦试验,无一例外,都是以战歌始,以悲歌终。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说,从苏联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与大肃反,到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和反右文革这样的灾难,从朝鲜建立三代金家王朝,到柬埔寨至少七分之一人口被红色高棉屠杀或迫害致死……都怪这个英国先知从一开始就开错了药方。但是重读《乌托邦》,我们不可能不以我们带血带泪的亲身体验悟出:对于一切强迫推行某种理想制度(哪怕是看起来再合理再公平的制度)的方案主张,应该拒绝,高度警惕。
“强迫”是个关键词!
正像诗人徐志摩访问过刚刚诞生不久的苏联后所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血污海,人类必须游过这血海,才能登上彼岸。
“必须”是个关键词!
俗话说:“好了疮疤忘了疼。”有些从中国的乌托邦幸存下来的人又怀念那段岁月,还有些人生得晚,没赶上经历浩劫,对那个乌托邦心驰神往,主张重新试验建构的大有人在。但我看,除了再经受一次浩劫,不可能有别的结局。道理不必我来多讲,就说一点:《桃花源记》也好、《乌托邦》也好,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笔下的理想国都有赖于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封闭隔绝——要么大洋浩瀚,要么关山险峻,要么通路隐晦,外人偶然寻访成功一次,也无法重复。

亚伯拉罕·奥特柳斯为《乌托邦》绘制的地图。乌托邦与外界是不相通的。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居民对于隔绝多少算是自愿,因为他们是“先世避秦时乱”“来此绝境,不复出焉”,对误打误撞来到这里的武陵人千叮咛万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可别对别人说!他们宁愿自我隔绝;而莫尔笔下乌托邦的与世隔绝,是统治者刻意为之。乌托邦当初并非四面环海,是开国君主掌权后,立刻争分夺秒发动超级工程,动员所有士兵和原住民挖断连接大陆的陆桥,使乌托邦成了海水环绕的岛屿。这反映出乌托邦人高度重视杜绝外患,同时也认定这是防御内乱的治本之策。莫尔写道:“任何人擅自越过本城辖区,被捕经查明未持有总督的文件后,遭遇是很不光彩的:他作为逃亡者被押回,严重处罚。任何人轻率地重犯这个罪行被贬作奴隶。”乌托邦,就得是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只有封闭,防范交流远行,才有他们所希望的稳定。
那么今天,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各国经济、资源、环境互为依存,重新闭关锁国太难了!像朝鲜那样,还能维持多久?
任何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也就是梦,不过有大有小而已。美国人有美国梦,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本次节目正赶上毛泽东的诞辰日。我不由得想起毛泽东的梦,他的理想国。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贯串着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有人说他就是个权力狂,根本不想别的,我看不是事实。
年轻时他醉心过一种“新村”;
他在诗词里面更是多次表述过绚丽的梦;例如在《念奴娇》中写过,把昆仑雪山“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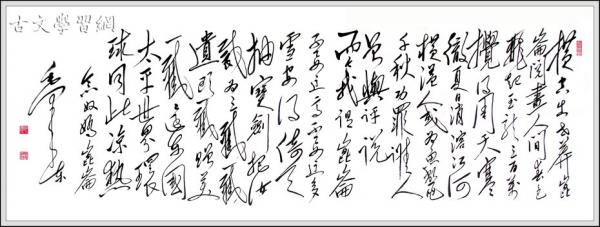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
建立红色中国之后,他屡次抒发对未来的向往——有时表达一种信念:“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有时写到梦境的壮美:“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有时带着某种怅惘:“借问陶令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时他又亢奋地相信理想已经变成现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不过这些都只是感情化、形象化的想象。在《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文章中,他对未来做过政治设计;但是真正系统地具体地勾画未来社会,阐明心目中的理想国,是1966年5月。
当时北京正风云变幻,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讨论“文革”战略决策、通过“五一六通知”,会议不可谓不重要。但是毛泽东竟然没有出席,置身事外。决策已经作出,意图已经传达,自有人去冲锋陷阵,他这个主帅,就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必还像1959年庐山会议一样,去面对面争辩、训斥、甚至骂娘了。他思考更为宏伟的规划、更为长远的未来。

毛泽东与林彪。
会议在北京紧张进行的第四天,即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杭州细细阅读林彪前一天报送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他拿起笔来,给林彪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几个月后在建军节时发表,这就是“五七指示”。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泽东《五七指示》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是一段极具纲领性的指示。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破”的纲领,这个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毛泽东自己是很重视“五七指示”的。2013年12月,文革中一度炙手可热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发表文章。回忆说1966年5月13日,也就是写下给林彪的信之后第七天,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江青也在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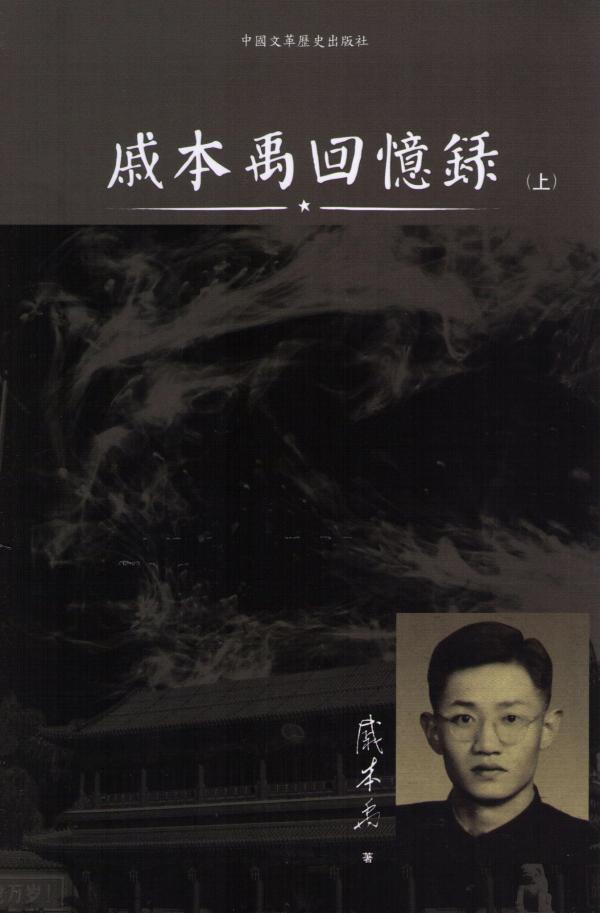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回忆了毛泽东如何重视《五七指示》。
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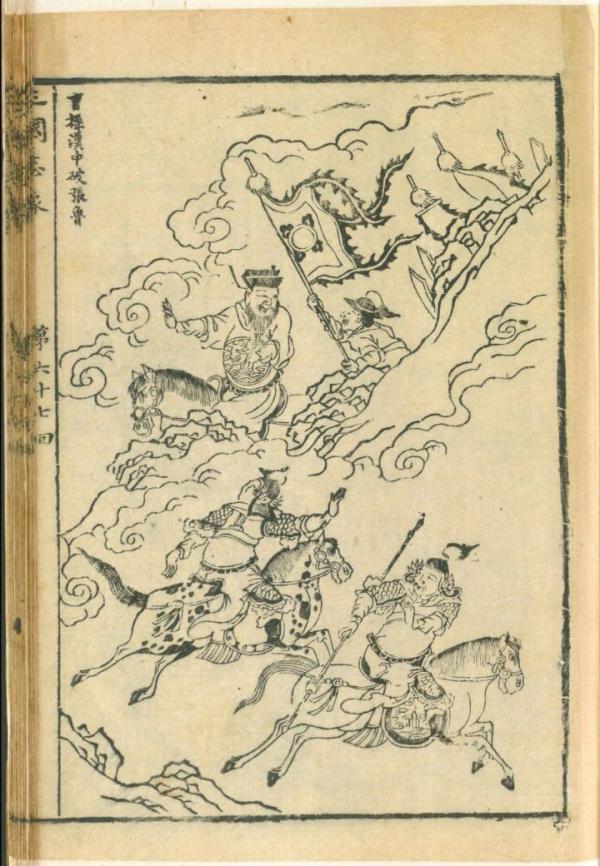
《三国演义》中记叙了张鲁。张鲁的社会设计引起毛泽东的向往之情。
戚本禹回忆,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1966年7月,陈伯达要戚本禹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五七指示”就是共产主义蓝图。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
具体规划了什么呢?毛泽东要另起炉灶,独创一个新的理想国模式,而不是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来一番改进。标志就是“人人一样”:思想一样,地位一样,职业一样——最多只是有主从之分。
根据“五七指示”,加上其他零零碎碎的“最高指示”,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的理想国大致是:把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变成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政企合一的准军事化组织。毛泽东抓住了现存的经济社会体系最基本最初始的因素——分工。有分工,才有差别,才有交换,才有商品与货币,才有形形色色的剥削乃至于国家机器。要反对这一切就不能修修补补,而要釜底抽薪——取消分工!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怎么消灭?毛泽东别辟蹊径:提低就高,既费力又费时;铲高填低,既省力又省时。与其让乡村赶上城市,让农民赶上工人,让体力劳动者赶上脑力劳动者,不如倒过来,让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人向农民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连城市、连脑力劳动、连现代工业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什么三大差别!
可以看出,这个理想国,混合了“乌托邦”、“桃花源”、“井田制”、“延安精神”等等。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党政军民学……人人都“一专多能”,事事都“自给自足”——任何一个成员,都是多种角色集于一身;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万事不求人”,都是一个个微型封闭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五七指示》发表后,宣传机器开动起来,大造舆论,但都是空洞口号。
文革之前,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指出中国政治的原动力,追求的是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革命”,一个目标是“现代化”。哪个更重要?毛泽东断言是前者,他要防止现代化取代了革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在七十三岁高龄之际,发动他这一生的第二件大事:为走向理想国扫清道路。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和青年,被选中成为毛泽东社会试验的试验员。他要同时达到两个目的:既搭建起理想国的脚手架,又锻练出理想国的建筑工。
但是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推出了一些举措,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立五七干校,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等等,后来都雷声大雨点小,搞不下去。毛泽东自己似乎也“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比起斗刘少奇批走资派批黑线回潮,文革中的“破”雷厉风行,但“立”就远远没那种声势。不仅如此,不管陈伯达戚本禹怎么高调评价,也不管那个年代人们如何狂热崇拜毛泽东,但毛泽东端出的这份共产主义蓝图,却吸引不了民众的眼球。学者胡平写过几篇文章,点出这实在是咄咄怪事:人们对这份五七蓝图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少得很不相称。就是在它发布的当时,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翻一翻五十多年来人们对文革的记述和回忆,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提到“五七指示”的微乎其微!
关于乌托邦,还有许多有意义的话题,不可能都谈到,这里我想简略地提一下,供各位读者都想一想。

《乌托邦》除了图书,还被改编制作成影视。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之后的五个世纪,又有《太阳城》《伊加利亚旅行记》等多部描写未来更合理、更理想、更光明、更幸福的社会的著作;被统称为“乌托邦”小说;这些小说出版之日,世界上还没有人进行过大规模的乌托邦试验。但之后,二十世纪,许多民族实行过公有制,有了惨痛的教训,随之而来,影响更大的是“反乌托邦”小说,代表作就是《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和《我们》,这三部书不约而同,都警告我们:凡是以强力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美好社会,最终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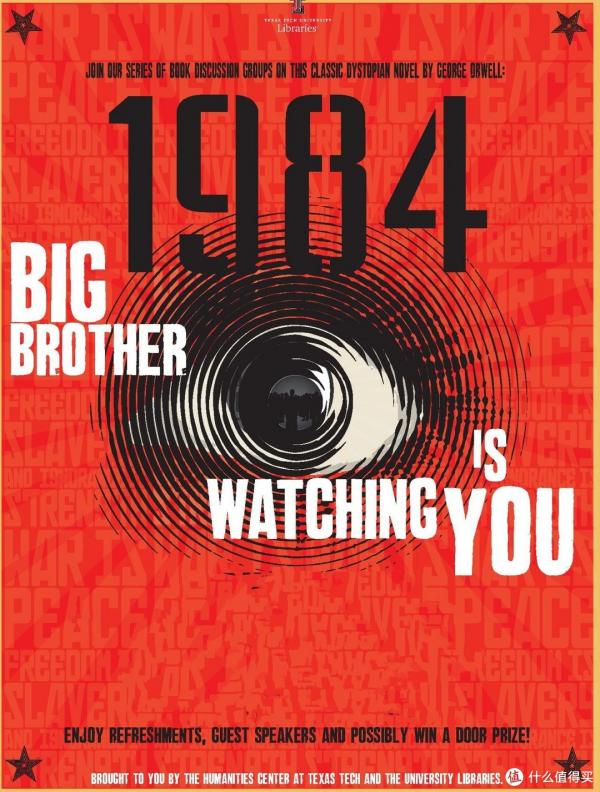
“反乌托邦”小说中以《1984》为突出代表。
到我们生活的今天,甚至可以说,人们对未来的描绘,几乎没有金红、蔚蓝和玫瑰色在闪烁了,都是漆黑、苍白和铅灰的交织,影响最大的科幻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不论是人工智能、时空旅行、外星人,像《黑客帝国》、《魔鬼终结者》,都是人类遭难;中国作家刘慈欣的《三体》想象雄奇,赢得国际科幻小说“雨果奖”,但最后的结局,是地球连同所有人类,以及太阳系全部毁灭。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类对未来的描绘,越来越悲观,越来越消极,甚至越来越绝望?人类已经黔驴技穷,提不出任何乐观、积极的设想了吗?已经没有能力想象和追求更光明、更幸福的未来了吗?以至于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回过头来,到毛泽东没有实现、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乌托邦社会试验中去寻找出路。让人叹息!

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气势宏大,描绘了人类连同太阳系如何走向毁灭。
我还想再说一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的具体设想虽然注定不可能实现,但是不满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应该说,是植根在人类的基因之中,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值得我们崇敬和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