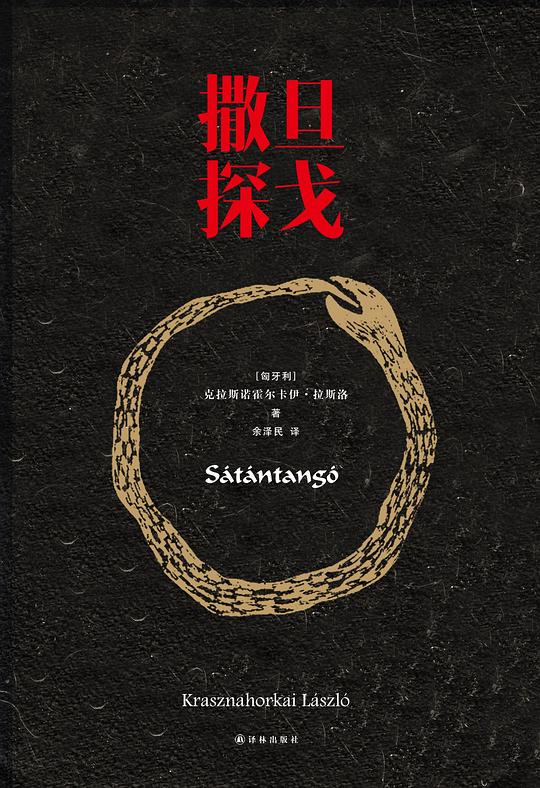这位匈牙利作家是个彻头彻尾的忧伤主义者:“没有什么理性的原因可以让我快乐起来,当我回顾人类的历史,有时我觉得是一出喜剧,但是让我哭泣;有时又觉得是一出悲剧,却让我微笑。”人类所有自以为聪明的努力不过都是在原地跳撒旦探戈
老高按:一如往年,诺贝尔文学奖接续次第公布的生物医学奖、物理奖和化学奖,排序第四,于美东时间今晨揭晓。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对获奖作家、匈牙利的Krasznahorkai László这个名字,既感陌生,更一时不知如何读。后来才知道,他的处女作、成名作和代表作《撒旦探戈》,早在1985年就出版,2017年在中国大陆就有了中译本,其中译者余泽民将他的名字译作“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还打趣地说:这位匈牙利作家的全名很长,我认识了他二十年,才勉强能一口气把它说出来:“说之前必须长吸一口气,说完后差不多断了气”。

这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国际文坛上成名已四十个春秋,获奖无数,匈牙利国内奖项拿了个遍,包括2004年的匈牙利文学最高荣誉——科苏特奖,2014年获美利坚文学奖,2015年获国际布克奖……他以长句子为名片,与以长镜头著称的匈牙利著名导演塔尔·贝拉,合作了多部影片,包括《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伦敦人》和《都灵之马》……据说都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
他多次访问中国,写下多部与中国有关的书籍,还有个中文名字:“好丘”,据称一来他与山丘有缘,二来他爱孔丘。
我没有读过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任何一部作品,也不了解他,今天早上得悉他获诺奖,才查了一下维基百科,也在万维博客上拜读了汪翔对他的介绍,很有收获。请点击:
汪翔: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随后我幸而得到中国大陆的朋友发来的有关资料,其中有《撒旦探戈》中译者余泽民为这部作品所写的序:《活在陷阱中跳舞》。转载于此,以飨同好。
老实说,读了这篇不短的序,我很可能不会进一步去读《撒旦探戈》:艰深得“简直就要憋死”译者的小说,我可以承认它是一道佳肴,却不是我喜欢的那盘菜;何况,译者在这里已经从作者到作品介绍得如此详细了!
《撒旦探戈》译者序:活在陷阱中跳舞
余泽民,《撒旦探戈》,译林出版社 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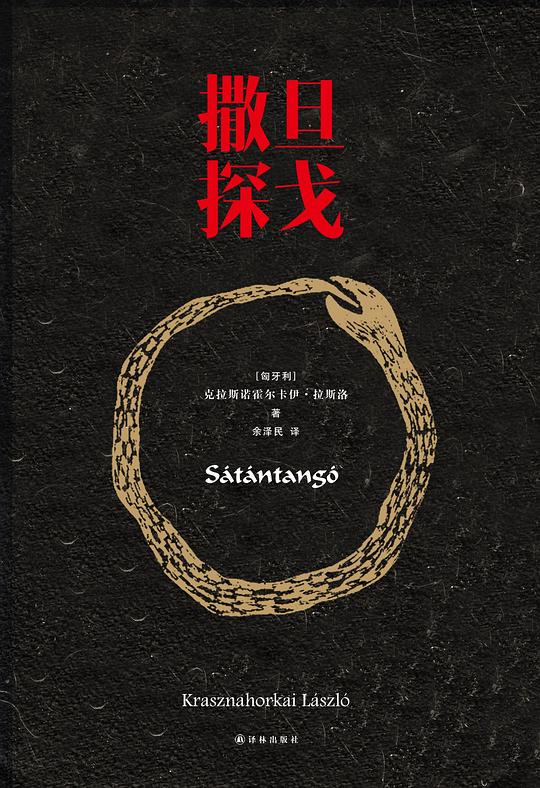
《撒旦探戈》
【匈】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中译者余泽民
1
终于,我像蛀虫啃石梁一般颇怀壮烈感地翻译完了这本虽然不厚,但绝难一口气读完的《撒旦探戈》,立即沉不住气地告诉了责编,与其说告捷,不如说告饶,若这书再长上几十页,估计我会得抑郁症的。读这本几乎不分段落的小说,就像读没有标点的古文,每读一行都感觉艰难。随后是一段刻意的遗忘,我将译稿旁置了三个多月,才又鼓起勇气重新拾起,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重读,校改,润色,定稿。译稿发出去后,我跟责编抱怨:“简直就要憋死我了!现在我真想跺脚,喊叫,砸东西,摔书,再也不想看到它!”
当然说归说,怨归怨,心里还是惦着我的这个译本能早一点印出,好让我揣着所有释放不掉的焦虑和愤懑再次把它翻开,换一个读者的身份再读一遍,当然,再焦虑一遍,愤懑一遍,绝望一遍,也再清醒一回。这本书于我,是一种虐读,全新的体验,折磨加享受,窒息式的快感;快感之后,是更持久的窒息。
十月末的一个清晨,就在冷酷无情的漫长秋雨在村子西边干涸龟裂的盐碱地上落下第一粒雨滴前不久(从那之后直到第一次霜冻,臭气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迤的小径变得无法行走,城市也变得无法靠近),弗塔基被一阵钟声惊醒。离这里最近的一座小教堂孤零零地坐落在西南方向四公里外、早已破败了的霍克梅斯庄园的公路边,可是那座小教堂不仅没有钟,就连钟楼都在战争时期倒塌了,城市又离得这么远,不可能从那里传来任何的声响,更何况:这清脆悦耳、令人振奋的钟声并不像是从远处传过来的,而像是从很近的地方(“像从磨坊那边……”)随风飘来。他将胳膊肘支在枕头上,撑起上身,透过厨房墙上耗子洞般的小窗口朝外张望,窗玻璃上罩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在幽蓝色的晨幕下,农庄沐浴在即将消遁的钟声里,依旧喑哑,安然不动,在街道对面,在那些彼此相距甚远的房屋中间,只有医生家挂着窗帘的窗户里有灯光滤出,那里之所以能有光亮,也只是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主人已经许多年不能在黑暗中入睡了,弗塔基屏住呼吸,生怕漏掉哪怕半声正朝远处飘散的铿锵声响,因为他想弄清楚这阵钟声到底来自何处(“你肯定是睡着了,弗塔基……”),所以他绝对不能漏掉任何一点声响。
这是《撒旦探戈》开篇的头几句。整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黏稠、缠绕、似火山熔浆涌流的句子,而且不分段落,让人读得喘不过气,恨不得一个塔尔·贝拉式的超长镜头从《创世记》拍到《启示录》,翻译完这本小说,我感觉从人间到地狱里走了一遭。绝望之后的绝望,没有人能逃出书中描绘的泥泞世界。这部作品有着宏大的构思、公式般精密设计的情节,环环相扣,密不透风,在那个阴雨连绵、广褒无垠的泥泞世界里,所有人都没有自主的空间,都是希望的奴隶,命运的棋子,包括作家自己,最终也与那个将自己关在家中昼夜偷窥并勤奋记录的医生融为一体,既操纵蛛网,也被蛛网绑缚。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有希望的人间,哪知人间在魔鬼的陷阱里;我们以为自己长脚就有可能逃离,哪知道自己是粘在蛛网上的米蛾。人类的历史就是周而复始,永难逃脱魔鬼的怪圈。
《撒旦探戈》,这书名对国内读者来说并不很陌生,因为它是2015年曼布克国际奖得主的代表作,后现代名著,匈牙利制造,而且作者多次来过中国;喜欢欧洲文艺片的国内影迷们更会知道,匈牙利著名导演塔尔·贝拉曾将这部小说改拍成一部七个半小时的黑白故事片,从头看到尾的人不多,但收藏它的肯定不少;搞电影的人更清楚,塔尔·贝拉导演的所有影片,无论是原著还是剧本,几乎都出自《撒旦探戈》的作者一人之手。这位匈牙利作家的全名很长,我认识了他二十年,才勉强能一口气把它说出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但说之前必须长吸一口气,说完后差不多断了气。据作家本人说,他的家姓是一个地名,在现在的斯洛伐克境内有一座始建于十三世纪的著名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城堡曾是匈牙利大贵族安德拉什伯爵家族的领地,2013年3月被一场“由两个男孩抽烟引发的大火”烧毁。
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有什么关系?有的,除了他的祖先可能来自那块地方,还存在着历史、文化、命运上的秘通暗连。不久前,我在匈牙利的“图书博客”上读到了一篇文化记者纳吉·伽布丽艾拉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采访,时间选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火灾的纪念日。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为那次对话铺设了某种背景或基调。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承认,火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可怕的组成,迄今为止,他曾亲身经历过六次火灾。其中一次,他与著名作家麦瑟吉·米克洛什在布达佩斯会面,圣安德列的家宅着了火;还有一次,他在一个乡村图书馆当管理员,由于图书馆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他失掉了工作,回到了城里,两年后水到渠成地写出了《撒旦探戈》,而且也跟凯尔泰斯一样,处女作一出手就抵达高峰,确立了他后来作品的反乌托邦主题与忧郁的基调,无论是后来的《抵抗的忧郁》《战争与战争》,还是新近问世的《温克海姆男爵归来》,都可以看成是《撒旦探戈》的续写。总之,火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元素或符号,被问及自己与那座同名城堡的关系时,他卖关子地回答:“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火灾是我生活的第七个阶段,我现在没必要告诉你它的意义。至于我的家姓和那个地方有什么联系,还是让它继续被青苔覆盖,保持它的神秘吧。”
2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书里书外都是纯粹的作家。从某种角度讲,他是一位演技相当出色的文学演员,时刻都在扮演一个绝无仅有的洞察者角色,就像《撒旦探戈》中因窥视而存在的医生,用冷酷的方式记录窥视到的一切(包括自己),他善于从生活中提取深层的意义,也擅长用隐喻讲述无意义的历史——周而复始,如封闭的魔圈,没有谁能挣脱掉,逃出去。医生自己也不可能,因为记录本身就是迷宫。
《撒旦探戈》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充满了神秘而冷酷的隐喻,在奠定自己文学风格的同时,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高峰。一个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复杂长句接力,缠绞,确如火山爆发时殷红的熔岩顺着地势缓慢地流淌,流过哪里,哪里就是死亡。小说的构架十分奇特,带着强烈的音乐性,有时让我听到谭盾的《火祭》,有时透出柴可夫斯基《悲怆》的韵律,虽然场景荒僻,但是叙事宏大,在沉缓、苦涩的叙事内部有着魔鬼般邪恶力量的指挥和驱动,正是这种撒旦的旋律像摆布棋子一样摆布着每一个角色,操纵他们的每一个步伐、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念头。
故事发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庄,那是一个曾经红火过一阵、现在已被废弃了的农业合作社,绝大多数居民陆续逃走了,逃到别的地方谋生,只剩下十几个人无处可逃,在阴雨连绵、一片泥泞的晚秋日子里演绎着酗酒、通奸、阴谋、背叛、做梦与梦破的活报剧。伊利米阿什来了!他的出现在村里人眼里无异于救世主、弥赛亚,点燃了他们绝望中的希望;他们欣喜若狂地追随他,跟着他跳起死亡之舞,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救世主实际是魔鬼撒旦。可悲的是,人类的智力赶不上撒旦,因此他们永远都不会醒悟。
这部小说的标题跟内容一样神秘而复杂,小说的结构也与书名紧扣。《撒旦探戈》的十二个乐章环环相扣,首尾连接,描绘了人类生活的可悲、绝望、惨败与毁灭,既充满了忧郁,也充斥着荒唐,否定了一切幻梦和希望。尽管也有短暂的麻痹和可笑的乐观,但最终揭示的还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希望是相对的,绝望是绝对的,一切都比绝望还更绝望。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没有留给人类任何出路。正如曼布克国际奖评委会主席、英国女作家玛丽娜·华纳所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并拥有非同寻常的热情和表现力,抓住了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生存状态,精细刻画出那些可怕、怪异、滑稽、既惊悚又美丽的生存肌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笔下的世界,充满了毁灭的喑哑与嘈杂。
从匈牙利到欧洲到世界文学,克拉斯诺霍尔卡伊都是令人仰望的星斗,不过他投射出的是阴影的黑光,投射到阴影的世界上,不是照亮,而是相反,让我们震惊于自己认知的懦弱。有人说他是悲观主义者,我说他是绝望主义者,至少在他的文学上。黑色虚构,又绝对现实,是后现代隐喻文学的代表作。
事实上,无论从1985年出版的处女作《撒旦探戈》到去年新问世的《温克海姆男爵归来》,还是从《优雅的关系》中从A向B、从B向C的连环跟踪到《抵抗的忧郁》中杀机隐伏的巡展鲸鱼,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所描述的都是一个阴影的世界,沉闷,诡异,绝望,惊悚,活在这个阴影世界中的人物都是阴影中的阴影,在偌大天宇下一个蛛网蔓延、被上帝遗忘了的角落里跳舞,向前两步,后退一步,撒旦的节奏,在原地踯躅。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一个主题,刻画人类生存的怪诞、冷酷、无情和绝望。他像一个预言家,预言了我们都不愿正视的未来。
或许并不算预言,只是推理,因为人类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或许,我们可以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看成凯尔泰斯作品的变奏,曾几何时,凯尔泰斯不也以奥斯维辛代言人的角色说,只要人类存在,大屠杀就会进行,因为大屠杀是一种人类文化,有墙的奥斯维辛虽被烧毁了,没有墙的奥斯维辛依旧存在,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和平的废墟。让世人直面人生固然残酷,但总比虚构人生更有意义,能让人活得明白并有所准备。难怪苏珊·桑塔格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比作果戈理和梅尔维尔。
3
我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相识在二十五年前,那时我刚漂泊到匈牙利不久,他也刚出版了那本名为“乌兰巴托的囚徒”的中国游记。他是1991年以记者的身份去中国的,中国政府邀请各国记者去中国访问,拉斯洛在华期间得到了周到、完美的安排,他的文字和他看到的面孔一样带着笑容。
我第一次见拉斯洛是在1993年早春,在匈牙利南方的塞格德市。那正是我最落魄的时候,没工作没钱没身份,寄宿在好友海尔奈·亚诺什博士家,准确地说是被他收留。亚诺什年长我十岁,当时在尤若夫·阿蒂拉大学(现塞格德大学)历史系任教,1989年后率先创办了一份在精英阶层影响甚广的文史杂志《2000》,成为文化名人,并以Q.E.D出版社社长的身份先后出版了由著名哲学家、翻译家兼画家库拉琼·伽博尔老先生翻译并作注的《易经》和《道德经》,他和拉斯洛是好朋友,出版过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优雅的关系》,现任匈牙利塞切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在当时,亚诺什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一大群大学师生、学者和诗人、作家在身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还是文学界的“当红小生”。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是亚诺什邀请拉斯洛到塞格德与读者见面,提前几天,亚诺什就一再叮嘱我,这个周末哪儿也别去,说要把我介绍给一位“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他还说,那位作家很想跟我聊聊中国。可以想象,他对作家也说了一套介绍我的好话。总之,那次会面是双方共同期待发生的,有朋友做中介,都带了美好的预期。
拉斯洛是个高个子,稍微有点驼背,总喜欢穿蓝色或黑色的棉布外套,最有个性的该算他常戴的黑色礼帽,长发齐肩,一副我想象中的田园诗人气质。虽然对一位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适合用“漂亮”来形容,但他确实长了一副兼灵秀飘逸、浪漫敏感、深邃成熟于一体的漂亮面孔,深棕色的络腮胡修剪得利落整齐,额头很高很宽,即使在冬天也晒得红红的,发际很高,那时齐颈的长发还没变灰白,唇须下挂着温善友好、能够融化陌生的微笑。说话的时候,他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湖蓝色的眼睛明澈透亮,透抵人心,既有孩子的真纯、成年人的狡黠、音乐人的热烈,也有思想者的深邃。我想,大凡第一次见到拉斯洛的人,都会被那双波斯猫般的眼睛和裘德·洛式的微笑迷住,他讲话的音调也温和、委婉,如同朗读自己小说中绕山绕水的长句。
拉斯洛说,他1991年第一次去中国,回来后写了一部散文体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我从中国回来,一进门就向家人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改用筷子!”他的英文讲得很流利,绘声绘色,家人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发神经,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场持续了多年的“中国病”。从那之后,不管他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有关的各种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和新闻。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闲聊,开口闭口都离不开中国。他尤其迷恋古代中国,崇拜诗仙李白,他自称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国味道”。他说:“只要在街上遇到一个亚洲人,尽管分不清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我都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好,我去过你们的国家。”
他给了我一张带中文的名片,上面印有“好丘”二字。他说那是他的中文名,是他上次去中国之前特意请一位汉学家朋友帮他起的,一是取“美丽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就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与孔夫子挂钩。虽然我觉得这名字不妥,但还是保持了善意的沉默。我能想象出中国人接到他名片时的微微皱眉,也能想象出他绘声绘色对自己中国名的得意解释,这名字怪虽怪,但很可爱。
虽然拉斯洛去过一趟中国,但在亚诺什家,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能够作为“朋友的朋友”近距离接触的中国人。拉斯洛是个情感丰富、善于表达的男人,不但知道如何被别人欣赏,也知道如何欣赏别人,尽管他极富阴柔与自恋,可一旦对谁产生兴趣,便会表现出无尽的耐心和溢于言表的情感,会用童话般的语调讲一段长长的小事,会用诗一样的词语赞美你。生活中的他,就像一位既迷恋自然又在乎自己的印象派画家,不失毫厘地观察日出日落的色彩,体验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然后将思维转换成文字,画到纸页上。
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聊到了李白,他说李白是他最崇拜的中国诗人,他读过许多李白的诗,要知道,科斯托拉尼·德热[1]、沃洛什·山多尔[2]、法鲁迪·久尔吉[3]、伊雷什·贝拉[4]、萨布·吕林茨[5]等多位匈牙利大文豪、大诗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翻译过李白的作品。叫他感到惊异的是,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在欧洲人眼里的“现代派诗人”?谈到兴奋之处,他要我抄一首李白的诗给他,我便用毛笔写了一幅《赠汪伦》,我不仅用中文吟给他听,还将大意翻译给他,他从书架上找到一本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匈文版《李白诗选》,还真找到了这首的译文。读罢,他点头微笑:“妙极了,这比兰波的情诗更动人。”我不知道兰波是否真给魏尔伦写过情诗,不过他的这个比喻让我会心地笑了,觉得这个人很浪漫,很敏感,很个性,很随意,在他思想的原野几不设防,也没约束。更何况,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暧昧的文体。
这天晚上,拉斯洛和我聊得投机,索性邀我随他一起回家小住几日,连夜开车带我离开了塞格德。当时,他住在北方一个叫乔班考的小村庄里,我在那里住了有一个星期。
4
那是栋盖在果园里的石头房子,感觉更像座图书馆。书架直抵天花板,其中两层是他从世界各地收藏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画册。出于好奇,我问他是怎么开始写作的。他给我讲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边城——久洛市(Gyula),父亲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久尔吉是一名律师,血缘里混合了法兰西和犹太人的历史记忆;母亲帕林卡什·尤利娅是血统纯正的匈牙利人,在地方政府做社保业务。少年时代,他曾是小有名气的钢琴手,是一支爵士乐队里唯一的未成年人,或许因为音乐,他身心充满了浪漫气息。在久洛市,他一直读完职业高中的拉丁语专业,而后先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学习了两年法律专业,准备子承父业。拉斯洛迷恋文学由来已久,1977年就在文学杂志《运动的世界》上发表过一篇《我曾相信你》,但那只是练笔,很少有人读过它。同年,由于忍受不了法学的冷漠和枯燥,拉斯洛转到罗兰大学文学院攻读大众教育专业。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当过思想出版社的资料员、编外记者,还做过地板打磨工。
那时的拉斯洛还是一位充满青春理想的社会主义者,揣着一股为大众服务的朴实激情。1983年,拉斯洛大学毕业,抱着用文化拯救贫困的热愿,主动离开都市,跑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沟里,当了一位乡镇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那是一个吉卜赛人聚居、被上帝遗忘的角落,镇子上虽有一所小学,但真正读书的孩子少得可怜。所谓“文化馆”不过是一幢低矮破旧的老屋,有一间办公室、一个储藏室和一间二十来平米的阅览室,藏书不过几千册,而且大多是纸页棕黄的旧杂志。旧归旧,但却很“新”,因为很少有谁摸过它们。四壁和家具都散发着霉味儿,书上落满了尘土,墙角和书架上蛛网密布,塔灰高悬,大概就像《撒旦探戈》中描绘的小酒馆库房。
在拉斯洛之前,曾有过一位图书管理员,据说是一个只在梦里清醒过的中年酒鬼。让酒鬼管书,倒也平安无事,直到有一天清晨发生了意外:这个酒鬼在从酒馆到文化馆上班的路上和另一个骑摩托的酒鬼撞到一起。拉斯洛说,幸好酒鬼被送进了医院,才给了他一个在别人眼里根本不是机遇的机遇。医生先给酒鬼接上几根肋骨,随后把他转到了精神病院。终于,小镇上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出现了一个新鲜的年轻人面孔。
拉斯洛到任后,将所有图书认真编目,并动手写了几十张通知散发到学校和居民家里。图书馆在一个跟往日没什么两样的上午重新开门。第一天没有人来;第二天没有动静;第三天只有邮递员来送给他一封家信。一周过去了,年轻人的激情开始降温。
有一天下午,拉斯洛坐在办公室的木椅上看书,忽然听到阅览室门口有些响动,他本以为是老鼠或捉老鼠的猫,撂下书到隔壁看了一眼:阅览室里静悄悄的,木门虚掩,什么活物也没有。他回到屋里重新坐下,刚把书捧起,又听到了响动。年轻人再次起身去看,还是没发现任何异样,不过这次他没马上走开,而是屏吸静气地站在阅览室中央。过了一会儿,他又听到窸窣的碎响,虚掩的木门被什么东西轻轻拱动……他冲了过去,拉开屋门,意外地看到一群灰头土脸的孩子!
孩子们被他怒气冲冲的样子吓坏了,四散逃开。拉斯洛抱歉地朝那几个躲在房后、树后的小孩子招手,孩子们用煤球一样漆黑的眼睛警惕地看他。拉斯洛想了想,回屋演了出空城计,不仅将木门敞开,还搬来一把木椅抵在门边,回到办公室重新坐好,手里捧着书,耳朵却机警地听着门口。慢慢地,孩子们又悄悄地聚回到门口,终于,第一个大胆的孩子试探性地跨进了门槛,另一个随后跟进来,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当拉斯洛从办公室走出来时,几十双眼睛盯在他身上。拉斯洛让孩子们围坐成一圈,给每个人发了一本书,用讲故事的方式给他们上了第一课,讲“怎样读书”。大多数孩子从没摸过书,于是他从书皮、扉页、作者、标题和插图讲起,然后讲读书的好处,告诉他们书里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再后,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童话《带刺儿的玫瑰》,绘声绘色地讲起来……那天晚上,阅览室里的最后一个孩子是被父母硬拉走的。
从那之后,拉斯洛开设了“读书课”,还从城里请来一些演员、作家跟孩子们见面。再后来,不仅是孩子,镇上不少成年人也成了文化馆的常客。图书馆逐渐变得热闹,常被孩子们挤得满满的;原来静如死水的小镇开始有了新闻和话题,有了惹人关注的兴奋点。在居民们眼里,新来的图书管理员成了一个奇特的怪人。不过,年轻人只在山沟里工作了一年,原因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午夜大火将文化馆连同可怜的藏书一起烧成了灰烬。既然没有了书,图书馆管理员也就失掉了存在的意义。于是,拉斯洛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小镇和孩子们。
“你们看,就是因为那一把火烧掉了小图书馆的几千册藏书。所以作为补偿,我应该多写几部。”作家曾打趣地跟朋友们说。失业后,他正式开始了作家生涯,用一年时间写成了处女作《撒旦探戈》,灵感就缘于这段特别的生活感受。拉斯洛善于描写封闭乡村的精神世界,能透过小酒馆里的琐碎场景看到人类最内心的层面。
在《撒旦探戈》里,伊利米阿什从城里回来了;在《战争与战争》的序篇里,先知以赛亚回来了;在《温克海姆男爵归来》里,又一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英雄再次出现在绝望者们的视野里,温克海姆男爵,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回到匈牙利,回到无望的故乡,在这里,人们等他就像等弥赛亚,等救世主。
绝望,希望,再绝望,再希望?
绝望的希望,希望的绝望;陷阱中的舞步,魔鬼的怪圈。
就像赫拉巴尔或艾斯特哈兹,他也在作品里通过东欧人特有的幽默表现事物悲喜剧的两面。在读者看来,《撒旦探戈》是绝对的黑色,但是作者自己并不承认。拉斯洛说,凡事都有悲与喜的两面,“从这面看是喜剧,那面看是悲剧。我们东欧人对这矛盾的两面格外敏感。实话实说,我不认为《撒旦探戈》是部黑暗作品,它不是悲剧,而是一部关于没有根据的信仰的悲喜剧。”
5
拉斯洛是一个看过世界的人。1987年,第一次离开匈牙利,拿着西德人给他的DAAD奖学金在西柏林生活了整整一年。柏林墙倒塌后,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不仅经常往返于德国和匈牙利之间,还先后旅居法国、西班牙、美国、英国、荷兰、意大利、希腊和日本,还有中国。
自从在塞格德相识后,他就一直跟我念叨,说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陪他再去一次中国。这个“中国计划”他酝酿了好久,直到1998年5月才得以实现。那一年,西欧的一家国际新闻组织从世界范围选出十二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请他们各选一位自己崇拜的人,然后沿着他的足迹实地游访,写一篇报道。与拉斯洛同在名单上的还有马尔克斯。拉斯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李白,决定沿着诗仙的足迹走一圈。我理所当然地做了他此行的随行、翻译和助手。
我们在五一节那天从北京出发,搭乘火车和长途汽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近十座古城,然后穿过三峡,抵达武汉。一路上进行了大量采访,每到一地,都要拜会作家同行,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跟中国文人谈李白并不是难事,他们总能谈出个“诗仙”、“酒仙”的所以然,甚至会为李白是“儒”是“道”争执一番。但是,试想一位蓝眼睛的老外和一个长发年轻人拦住一位过路的老农、商客、军人或年轻情侣,然后冒昧地提问:你知道李白是谁吗?你能背李白的诗吗?你为什么喜欢李白?你有没有听说有关李白的传说?作为中国人,李白对你有什么意义?假设李白坐在你的旁边,你最想跟他说什么?最要命的是,最后还要加上欧洲式的浪漫:“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做过情人吗?”
你一定能够想象出被采访者们当时莫名其妙、瞠目结舌、甚至忍不住喷笑的表情和录音机里录下的一句句不知所云又常出人意料的回答吧?
起初,我也觉得拉斯洛的采访很搞怪。李白写过诗千首,但大多数中国人能顺口背出的总是那首并非上品的“床前明月光”;李白走过无数山川,但我们所能找到的,只有后人附庸风雅的题字和为开发旅游而翻修的庙宇。我忍不住问他:“如果你在布达佩斯街头被一个中国人拦住问:你知道裴多菲吗?裴多菲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你肯定也会发愣,然后尴尬地发笑。不是吗?”
拉斯洛狡黠地笑道:“你说的不错。但是只要你追问下去,我总会说出点什么的,即使说‘不知道’,也是一种回答。”我耸肩默认。的确,一个中国人说“不知道”与一个欧洲人说“不知道”意味不同,或许,一个中国人在留有李白足迹的地方说“不知道”比随便一个中国人说“不知道”更能激发他的灵感?
旅程结束,在花了两周时间整理完我们录下的十四盘磁带之后,我才发现他的过人之处:作为外国人,他要捕捉的并不是诗人生前的地理行踪,而是作为诗人在本民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记。他要写一篇关于李白灵魂的文章,不是向欧洲读者介绍生平,而是讲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诗人。根据这次旅程,他写了一篇散文体长游记《只是星空》。回到布达佩斯后,我对朋友的作品产生了好奇,毕竟他是我近距离接触过的第一位作家。说来也巧,亚诺什刚好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优雅的关系》,顺手给了我一本。我不但翻着字典读了,还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将其中一篇《茹兹的陷阱》翻译成中文,几年后发表在《小说界》上。现在回过头看,那是我文学翻译生涯的起点。
以前我就很喜欢读书,但过去读书大多迷恋于内容,翻译《茹兹的陷阱》让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第一次被如此艰涩、精密、缠绕的语言所吸引,越是难读,越是想读,感觉到读书的蹦极状态。这篇小说译成中文只有一万字,但让我染上了翻译的瘾,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翻了三十多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为未知的未来做准备,直到2002年秋天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奖。从那之后,命运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不仅成为翻译家,还成了作家,从这个角度讲,他和凯尔泰斯都是我的文学恩人。
回想二十五年前,当我们初次相识时,他就兴冲冲地将一本散文集《乌兰巴托的囚徒》送给我,当时我一句匈语都听不懂,更不用说阅读了,我跟他只能用英语沟通。我问他《乌兰巴托的囚徒》书名的来历,他尽量简单地告诉我,1991年他从蒙古转道去中国,过境时签证遇到了麻烦,曾被困在乌兰巴托。说来真是缘分,当初我俩谁都不曾料到,二十五年后我会翻译他的作品,会充当他的中国声音。
其实对中国的出版界来讲,本来不该对拉斯洛感到陌生,他自九十年代后多次来过中国,造访过多位作家和编辑,我也无数次推荐过他的书,他学中文的妻子也来中国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最终都是不了了之。从2005年开始,我在《小说界》杂志开设“外国新小说家”专栏,第一期介绍的就是他,发表了其小说《茹兹的陷阱》。两年后,我又发了他的一篇《狂奔如斯》,可惜出版社的嗅觉并不灵敏,或是知难而退,直到他获得了曼布克国际奖才蜂拥而至。拉斯洛迷恋中国文化,除了《乌兰巴托的囚徒》外,还写过两部关于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书:《北山、南湖、西路、东河》和《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后一本书中有一篇《奶奶》,写的就是我的母亲。每次他到北京,都会住在我母亲家。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那将是他与他推崇的中国文化的对话。终于曼布克国际奖圆了他的这个梦,使他在中国变得抢手,我既为老朋友高兴,也为中国读者稍稍遗憾——本来十五年前就该读到他的作品。
6
2015年宣布的曼布克国际奖,使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站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在那之前,他于2014年获得了美国文学大奖,早在1993年,他就因《撒旦探戈》在德国被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而蜚声欧洲。他在匈牙利获的奖更是不计其数,囊括了科舒特奖、共和国桂冠奖、马洛伊奖、尤若夫·阿蒂拉奖、莫里茨·日格蒙德奖、阿贡艺术奖等几乎所有奖项。
当然,无论奖项让作者如何走红,都改变不了作品的难度。无论对哪国的译者来讲,翻译拉斯洛的书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作家极富个性的文学标签就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即便描述穷乡僻壤的阴雨和泥泞,用“史诗般的”来形容他的语言也不过分。在拉斯洛看来,短句简单无趣,能承载的东西有限,当一个人思维奔涌、表达欲膨胀时,肯定会选择用长句,就像酒馆里的客人一样喋喋不休,不使用句号,一晚上只说一句话,当然,作家的唠叨与酒鬼不同,与表现欲一同膨胀的还有文字的野心与诗意。即便在母语文学中,他的长句也独树一帜,对绝大多数的匈牙利读者来说也是阅读上的挑战,他的句式既很难读又很耐读,细腻又粗粝,细碎又宏大,构设精密,富于律动。如果翻译不好,会让人读起来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因此不难理解,接连两届的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都颁给了他的英文译者和他的作品,2014年是《撒旦探戈》,2015年是《西王母下凡》,评论家们认为两位译者“发明了一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英语”。翻译成中文后也是如此,读者会读到一种有异于中文语言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中文”:
秋日的虻虫围着破裂的灯罩嗡嗡地盘飞,在从灯罩透出的微弱光影里画着藤蔓一样的“8”字图案,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撞到肮脏不堪的搪瓷面上,随着一声轻微的钝响重又坠回到它们自己编织的迷人网络里,继续沿着那个无休止的、封闭的飞行路径不停地盘飞,直到电灯熄灭;一张富于怜悯的手托着那张胡子拉碴的脸,这是酒馆老板的脸;此刻,酒馆老板正听着哗哗不停的雨声,眨着昏昏欲睡的眼睛盯着飞虻愣神,嘴里小声地嘟囔说:“你们全都见鬼去吧!”
读这样的长句,与其说是中文,不如说像太极拳,缜密沉着,缠绵不断,节节贯串,丝丝入扣,是中文写作者凭中文思维不大可能写出来的中文。难怪以长镜头著称的匈牙利导演塔尔·贝拉,在创作上离不开拉斯洛,从1987年至今,他俩已经合作了九部影片,不是由拉斯洛亲自改编自己的小说,就是由拉斯洛创作剧本,特别是《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伦敦人》和《都灵之马》,全都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仅从上面抄写的这句话,我们就可窥见他们俩的关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为塔尔·贝拉式长镜头的电影语言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文学支撑。读他的小说,感觉就像看塔尔·贝拉执掌的镜头如何以几乎静止的缓速慢慢地摇动:流向远方的泥泞,淅沥不停的阴雨,平原上黑暗的光线,贴在玻璃窗上的面孔,单调执拗的钟表嘀嗒,喋喋不休的一句醉话,手风琴拉出的探戈旋律,倒酒喝酒咂吧嘴的声响,在疾风中沉闷至极的行走,牛叫,数钱,跳舞,窥伺,夹着僵硬死猫的女孩,还有教堂废墟里幽灵似的疯子……无论镜头固定多久或推移得多么缓慢,都无法把我们带入任何的精神世界,所能看到感到的只是毁灭、恐惧、绝望和欺诈。
“首先,《撒旦探戈》在电影史上以片时最长、承载事件最少而出名:在这部七小时半长的电影里,除了一场骗局之外几乎没发生任何事情。对运动的想象在其自身中消散,将我们带回起点。”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这句评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小说的书名,“撒旦探戈”,陷阱中周而复始的魔鬼舞步。
在这部小说里,骗子是最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人,所有渴望活下去的人都麻木、猥琐、愚蠢,如跑转轮的老鼠。貌似发展的人类永远不会吸取任何的经验教训,一次次微弱希望的萌发,总以落入陷阱结束,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这部代表作里,骗局是未来的同义词,谎言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影片里,一行满怀憧憬的逃亡者在猫头鹰的凝视下,被“救世主”伊利米阿什引上迷途;小说的结尾,医生用木条将自己房间的门窗钉死,告诉我们“无处可逃”。尽管这部小说采用了形式主义特征强烈的后现代写法,但本质是冷峻的历史唯物主义。准确地讲,是部深刻的寓言小说或哲学小说。正因如此,就连目光高冷、吝啬口舌的苏珊·桑塔格也被他折服,称之为“当代最富哲学性的小说家”,是“能与果戈理和梅尔维尔相提并论的匈牙利启示录大师”。德国当代名家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视野的普世性,只有果戈理的《死魂灵》可以与之相比,远远超过了所有当代写作的短浅关注。”
另外,作者对卡夫卡的崇拜和继承也不言而喻,在《撒旦探戈》的正文之前,他用卡夫卡《城堡》中的一句话做引言:“那样的话,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它。”他多次在采访中明确地说,卡夫卡是他追随的文学偶像。我在他的文字中还能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他在作品里展现了贫困、绝望、污浊和黑暗之后,并没有给出解脱和救赎之路。
拉斯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忧伤主义者,即便生活中的他不缺爱情也不乏成功,他属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那类严肃作家,也许今天会被许多人讥笑,认为他杞人忧天,庸人自扰。他写《撒旦探戈》的时候,觉得“当时的世界太黑暗”,但是现在,他也认为世界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人类仍活在自己铺设的陷阱里,总是欺骗与自欺,这让他感到忧伤,甚至怀疑幸福。
“幸福是什么?是爱吗?我觉得不是,爱是痛苦的。”有一次,他带着那副招牌式的波斯猫目光和裘德·洛式微笑跟记者讲,“幸福只是一种幻觉,也许你确实能幸福上那么一两分钟,但在之前和之后都是忧伤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性的原因可以让我快乐起来,当我回顾人类的历史,有时我觉得是一出喜剧,但是这喜剧让我哭泣;有时又觉得它是一出悲剧,而这悲剧却让我微笑。”人类以为自己很强大,强大到能够挣脱上帝,但他们逃不出魔鬼的圈套,所有自以为聪明的努力不过都是在跳撒旦探戈,在原地踯躅。无处可逃!这是作家对整个人类提出的警示,不过,也恰恰由于作品的残酷和不留出路,为唤醒个体对普世的思考提供了一种严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