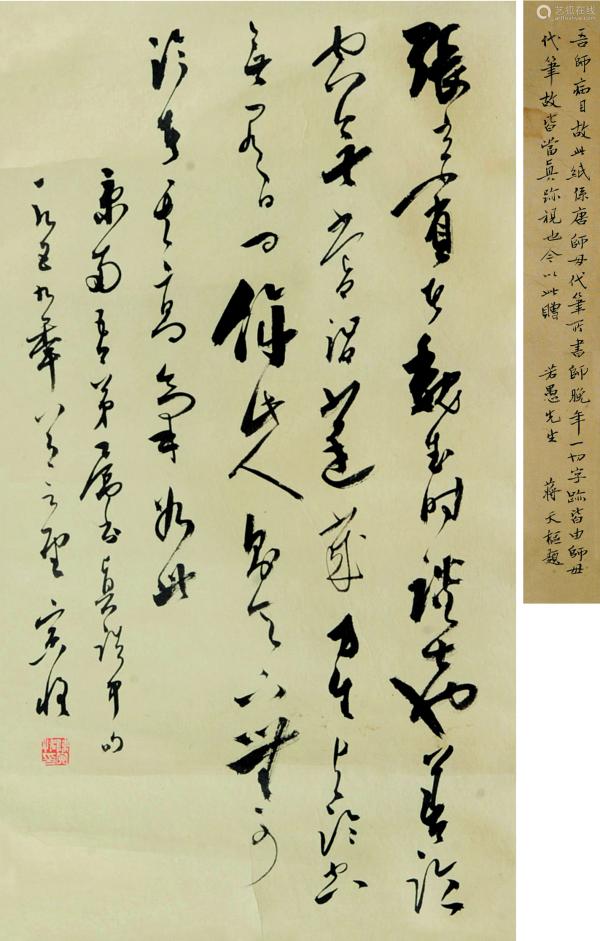| 《陈寅恪学问之“不古不今”》 其一 |
| 送交者: 2023年05月31日19:15:2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
|
俞频
三年前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年之际,国内学界和媒体推波了一股“陈寅恪”热,这也促成了当代重新仰慕民国学者以及学界对先生研究领域的再度审视而至今不衰。前几年陆键东先生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很热销,因为作者从事文艺写作专业,对于陈先生晚年在中山大学完成《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只是肤浅叙述而已,其实这两篇著作即便今天放在京沪高校的学研“领头羊”的书桌上也只有擦汗的份。我们在提到陈先生时一般冠以“国学大师”这一笼统称号,至于“国学”的感念至今依然含糊其辞。其实绝大多数人未必了解陈先生的专业领域,学术成就,甚至当代是否已经超越先生?还是“高山仰止”仰慕先生也全然无知。 首先我们从陈先生的学习经历逐次分析,陈寅恪先生的少年时代在他父亲主办的私塾里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功底,1902年随兄长留学日本考入私立名校庆应大学预备课,1909年由亲友资助留学于德国柏林汉堡大学,后转学于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在这五年里他主攻印度语和梵文。这里有个史料需要提一下,他于1912年末至1914年秋就读于巴黎大学期间,与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有过交往。伯希和最让欧洲汉学界轰动的是在1908年2月从敦煌千佛洞里取走了六千余卷极其珍贵的手抄卷子。法国政府特为他在法兰西学院设了一个中亚语言,考古教授席位。1911年他正式就职讲授敦煌文献。陈寅恪第二年与伯希和结识,有机会接触到敦煌文献,引发他进一步了解西洋东方学的欲望。但是欧洲一战爆发中断了陈先生留学也结束了与伯希和的交往。1919年1月受官方资助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再次转往德国柏林汉堡大学亚洲研究院,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穆勒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这期间他通过对于德国所谓的考察团其实就是掠夺敦煌,新疆吐鲁番佛教梵文残本文献的考证,成为梵文文献的研究专家。陈先生在漫长的留学时代从没有把学位和完成毕业论文放在第一位,这样的结果是他本人在世界学术界缺乏应有的地位但同时他能腾出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和研究。严格的说他学习的专业是中亚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是中世佛教梵文的考证。而他给后人留下的足以奠定他学术地位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这些著作和他专攻学科又是格格不入的,陈先生本人对自己的研究有过自评,收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之中: “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 湘乡南皮”是晚清的曾国藩和张之洞的出生地,后辈学者对陈先生的“不古不今”的意思争论很大,也可叹后来先生对此也不多说一个字加以解释。笔者经过多年的阅读,大致梳理出“不古不今之学”的三层意思,其一之治学的历史时段。其二之治学方法。其三之治学的对象及其开拓性。以下分段加以分析讨论。
其一,陈寅恪先生对国史的研究主要立足于隋唐史,他不碰古代史也不碰近代史谓“不古不今”。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解释了陈先生不碰古代史的原因:因为古史资料每多残缺,难有定论;而清末民初以来,疑古之风甚炽,学者不免常凭己意臆测武断。陈先生当时赞同“整理国故”但反对“整理”的方法,1931年陈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写道: “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这段话暗批的就是胡适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陈先生在这里提到的“穿凿附会”,举出的证据是“今日之墨学者”也指胡适先生。梁启超曾有公开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胡适治墨子多褒扬,对胡适谈孔孟多商榷。在当时学界影响很大,陈先生不可能不知。他认为“今日之墨学者”未免“穿凿附会”,是暗示胡适在谈墨子时用当时西方流行的观点来附会墨子。可是1965年晚年的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中写道:“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可见陈先生对胡适就事论事含有“惜才”之意,前者体现的是陈先生的“华夏文化本位论”,后者体现的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不碰近代史和他的家庭不无干系,祖父陈宝箴是可以写在清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太平天国事件时期曾以曾国藩的幕僚振济灾民筹备军需后勤,甲午战争期间陈宝箴官授直隶布政使在京商讨兵略,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后,陈对李害怕朝中议论畏罪塞责大为不满。之后受兵部尚书荣禄举荐陈宝箴诏授湖南巡抚,官场生涯达到顶峰,陈在湖南任官多年,熟知地方民情百姓爱戴,功绩名声昭赫乡里。戊戌变法时期,陈在湖南位上全力推动维新,后因变法失败而革职。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是光绪进士,是江西诗派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代诗人,因戊戌变法受家族避祸牵连很少参与政治,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寅恪先生晚年关注明末清初的大诗人钱谦益而著出《柳如是别传》多少是受他父亲影响,他热衷推诚的“以诗证史”的钱谦益思想也有他的一脉传承。1924年陈三立隐居杭州会见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当时徐志摩是他们的会见翻译,可见当时陈三立作为旧体诗代表在文坛的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因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去满洲国辅佐溥仪称帝而痛骂郑断然与之绝交。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陈三立拒绝逃难,眼见国土沦丧,陈三立悲愤交加,在淞沪抗战爆发的一个月后绝食离世。陈寅恪先生受聘于清华国学院“四导师”是1925年,在之后的短暂而难得的学院研究期后的抗战爆发,陈先生经历了失父之痛和颠沛流离地逃亡生活,1938年的“失书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研究领域。陈先生悲恸过度和右眼几乎失明使他放弃了应聘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一职,1941年在香港大学被聘客座教授后因沦陷而受辱于日本占领军和傀儡政府,直到1948年国共战争的北平危机而南下广州,最后陈先生是在文革的洪流将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洗劫一尽的悲愤绝望中离开人世。从陈寅恪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不难看到,陈氏家族和中国近代史的千丝万缕,尤其是祖父更是晚清大事件的参与者,而他又活生生地经历了1949年前后的“大历史”。陈先生始终认为带有个人情感来研究历史是偏离历史本质的,他说到也做到。同时1930年他自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而直到1938年后才涉足隋唐研究,简单地判断似乎这里的“不古不今”和隋唐没有关系?其实应当指出陈寅恪先生隋唐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之后,而陈先生的史观是一以贯之的,陈先生从不对近代史作任何批评或立书,不留任何语言或文字,这也是他对历史公正的最好维护和一个史学家难得的良心。 < 待 续 > |
|
|
 |
 |
| 实用资讯 | |
|
|
| 一周点击热帖 | 更多>> |
| 一周回复热帖 |
| 历史上的今天:回复热帖 |
| 2022: | 假装信却又不真的信,假装爱却又不真的 | |
| 2022: | 习近平什么时候动手? | |
| 2021: | 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 (二):遇罗克的《 | |
| 2021: | 人的家庭观念为什么重要 | |
| 2020: | 媒体要为人民服务 | |
| 2020: | 52O声明 | |
| 2019: |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 | |
| 2019: |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支持的反华措施 | |
| 2018: | 论毛泽东系列之七:毛泽东的骄奢淫逸是 | |
| 2018: | 川普开打贸易战 习王体制经受极端考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