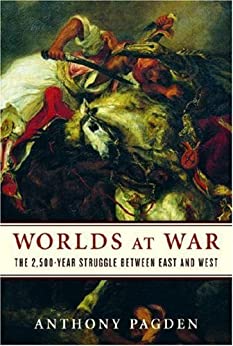思芦
《两个世界的战争:东西方2500年的较量》读书札记
《两个世界的战争:东西方2500年的较量》是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戈登2008年的著作。书中的东西方,指欧亚大陆的东西部分,欧洲和亚洲。广义的西方是超越了欧亚大陆,以英美代表的西方文明。作者讲述了自波希战争开始的东西方之间的战争史。分析东西方之间存在的永恒的敌意以及持续冲突的根源。对东西方实力此消彼长的历史和原因做了详尽的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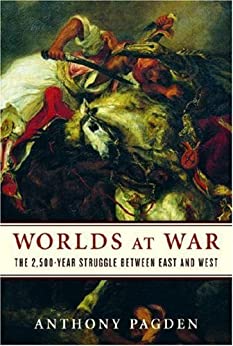
作者说很多西方的文明发源于东方,比如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就在亚洲的新月沃地,西方基督教也发源于位于中东的犹太教。基督教起源于中东。甚至后来成了欧洲扩张主义的核心特征的普世主义,也起源于波斯的帝国扩张。十字军东征的理念也源自于伊斯兰教的圣战。
书中波希战争的两方,和今天东方西方对垒有些相像。一方是庞大的东方专制主义,另一方是分立的城邦(规模和资源极其有限,但是因为是自由的个人而士气高昂)。双方兵力对比是10:1以上。在历史上,精神力量对规模数量的优越从未如此明显。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波斯人最大的特点是盲从和缺乏反抗精神。他们敬畏自己的统治者,并把他当作神。虽然波斯人看似勇猛、凶残,但实际上却贪婪、奴性重、讲尊卑、思维狭隘,缺乏个体能动性,与其说他们是一个民族,倒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个牧群。东方人被视为一个由恐惧驱使的民族,无法自由做出选择。东方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既不是像西方的君主国那样诉诸荣誉,也不是像共和国那样诉诸美德,他们的手段是使人心生恐惧。
一位波斯将领告诉他的希腊朋友,他完全清楚波斯人会失败。当被问到他为何不做些应对之策时,他回答道:“我的朋友,神决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要听命于我们的统帅。”体现了东方人在面对无法改变的事情时的被动心态,也表现出了波斯人当必须要告诉国王令人不快的真相时的胆怯。
希罗多德说,波斯人在波希战争失败之前,曾经有过一次“政体辩论”,他们有机会采取希腊人的民主治理方式,但是拒绝了,因为这不符合波斯传统。尽管波斯人可能乐于接受“异族的方式”,但这只限于埃及的服式。如果要放弃自己的传统,他们则会愤愤不平。他们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这种种族中心主义使他们异常脆弱,无法接受外界任何形式的批评,看不到自己的传统和习俗中的缺点,也无法改变或适应环境,这将成为他们最终毁灭的原因。
生活在西方的各个民族经常出现纷争,但是他们也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他们热爱自由超过生命,他们服膺法律。希腊人正是因为可以自由地争论、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才成为优秀的战士。奴隶在战场上选择逃避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只是在违背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情况下为他人而战。与此相反,自由人即使是在为他们的城市而战时,实际上仍然只是在为他们自己而战。
温泉关、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役确保了欧洲永远的自由。如果取胜的是薛西斯,那么波斯人将占领希腊,把希腊城邦变成波斯帝国的行省。那么就不会有希腊的戏剧,也不会有希腊的科学,没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而为后来的欧洲奠定基础的雅典文明也永远不会出现。
无论高卢人、西班牙人,还是埃及人,都可以说出那个有名的句子:“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 )。”无需进一步说明自己的地方身份。无论身处何处,任何罗马公民在没有得到公正审判的情况下受罚,他都可以“诉诸人民”,而皇帝正是其代表。在古代世界,只有罗马公民享有类似于人身保护令的权利,免受被武断裁决的伤害。可以说,并不是罗马人要扩张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的居民扑到罗马人的怀里,恰如后来的美国。在法律上,罗马公民身份是对统一身份的普遍要求。它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是希腊人自由和正义的基础。但是权利(它可能是西方世界所有政治和法律词汇中最重要的一个)的概念归根结底是罗马人发明的
征服容易,统治难。统治有赖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即使他们只是勉强如此。
罗马人从自己长期管理一个庞大帝国的经验出发,演化出一套复杂的法律体系。随着帝国的扩张,它成了全欧洲的法律,这是罗马人伟大的智识成就,可与希腊人在道德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相提并论。罗马法源自十二铜表法。自此之后,所有习惯法都需要有立法基础,以成文法典的形式颁布。它确保了罗马和后来以英美代表的所有西方国家里,法律是世俗而且独立的。这一点显著不同于亚洲绝大多数民族的法律,比如伊斯兰的教法和中国皇帝的诏书。罗马法不是神圣而不可更改的。它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调整,其原因被后来罗马的法学家多次强调:法律源自事实。法律的基础是习惯和实践。如同谚语所说的,人民的声音即神的声音(vox populi, vox dei ),而不是用神的声音对人民说话。它的基础不是理论,而是“事物的经验”。因为事实和存在的性质可能改变,因此它可以被修改。教法虽然也是人类的产物,但是它依据的并不是成文的习惯法,而是神的话语。因此,它很难被修改。神,特别是一神教里的神,不习惯改变想法。
大部分基督徒认为上帝允许人们自由地运用理性,这样他就会清楚地知道以何种方法才能实现幸福和人类的成就。从根本上说,真正重要的是理性和自由意志、个人选择的权利和能力,而非神的命令。基督教区别了世俗的和归上帝的事物,而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古代的多神教都没有类似的区分。多少有些矛盾的是,正因如此,两个本质上是世俗的和异教的概念一直存在于基督教的核心位置,它们分别是包含全人类的普世主义和个体的尊严与自主。
西方的争吵并不是软肋。进步是和内部冲突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康德所说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即所有人都有的竞争欲望,就不会有科学进步,实际上也不会有任何进步。最终,欧洲人长期无法逃避的不稳定性,恰恰成了他们最大的优势。他们的战争、无休止的内斗、宗教争论,所有这些都是不幸的,却又是知识发展的必要条件,与亚洲的邻居们不同,知识的增长将会使他们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探究态度面对自然,这反过来给他们带来了改造和控制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能力。罗马历史学家萨鲁斯特主张,维系共和国的并不是文明世界的统一,而是罗马内部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的斗争。自由在冲突中繁荣,它会带来进步和人类境况的不断改善。科学、知识和艺术只有在激励竞争、承认辩论的价值、注重理解而非背诵、鼓励人们自由交流的社会里才能够得到发展。希腊人拥有这些品德,在各个重要方面都是希腊人的继承者的罗马人同样如此。这成了欧洲的天赋。
无孔不入的神权阻碍社会。奥斯曼不能引进印刷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印刷的圣书,就不再神圣了。如果引进公共时钟,他们的宣礼员和古老仪式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那些即使只是对伊斯兰教的地位和《古兰经》的纯洁性构成稍许威胁的东西,都是不可接受的。对所有明显属于基督教的事物的仇视导致欧洲医学和其他科学被拒之门外。在穆斯林的头脑中,笛卡尔、开普勒和伽利略的作品与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一样,都是错误的和无关紧要的。
一旦穆斯林被说服支持平等、个人自由、自我表达的权利和其他西方社会词语,他们就会将曾经的生活方式视为原始和残忍的。对话和相互理解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西方化。
东西方超越了地理,是观念上的差异: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在很长时间内被东方游牧民统治着。它因此保留了很强的东方专制主义色彩,被德意志哲学家莱布尼茨称为“北方的土耳其”,被视为亚洲的一部分。罗马人认为,希腊人从他们“东方”邻居那里吸收了太多东西。他们无知、爱争吵、举止粗鲁,似乎为伏尔泰的一个观点提供了鲜活的例证:专制主义能将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变成奴隶。
中国文明停滞、过于讲究、过分注重仪式、无力创新或进步。如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所说“欧洲的五十年,胜过中国的千百载”。中国是一个一成不变、与世隔绝的帝国;不管居住在各个行省的人有多大的差别,他们都受到古老的体制原则管理,他们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极度服从。他们都以不同的形式被专制君主统治着,他们的政府系统受宗教或准宗教的束缚。他们的社会是由群体而非个人组成。穆斯林回头看他们的圣书;中国人回头看他们的历史和圣人的著作。因为孔子没有声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因此他的作品不同于穆罕默德的作品,也正因如此,中国社会比伊斯兰世界更现代。但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中国南海的整个亚洲,都将自己的面庞彻底转向过去。
习近平浅薄无知,暴发户心态,小富即狂,认为世界大局东升西降,现在是中国可以挑战世界秩序,实现世界霸主地位的机会。审视历史和现实,可以看清现代东西方的实力无论从硬实力来看,还是从软实力来看,现在说东升西降都是痴人之梦。今天中国的与西方硬实力对比,远远没有超出历史上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曾经的压倒优势。从软实力上看,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和体制的不同,也没有实质的改变。习近平如果发昏,当年波斯舰船在萨拉米斯海面樯橹灰飞烟灭,奥斯曼帝国在维也纳之围后的土崩瓦解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