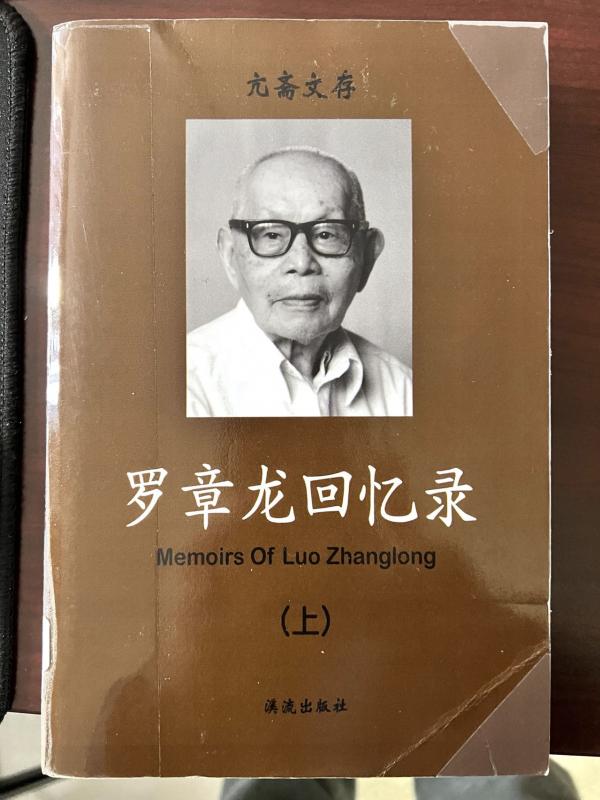抛开当了六年、又刚刚第五次当选连任的总书记,换上另一个更缺乏政治经验的书生掌舵——在钦差大臣操纵下,号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重演了中国专制历史上的宫廷政变,撤消合法中央,另立非法中央。这一恶例一开,百年历程中竟接二连三
八七会议:力挽狂澜的转折还是首次红色宫廷政变
《伐林追问》第131期,2020年8月7日首播
◆高伐林
今天是2020年8月7日,中共举行八七会议,已经93周年了。
我最早见到的中共革命纪念地,就是位于汉口鄱阳街的“八七”会议旧址,离我家只有咫尺之遥,三五分钟就走到了。而其它那些中共革命纪念地,什么南湖红船、遵义红楼、井冈山八角楼、延安窑洞、中南海菊香书屋……对于我来说都只是传说而已。不过直到“文革”中期,我才接触到一些资料,了解这个八七会议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个会议旧址搞成纪念馆,我去参观过。但真正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立体的思考,还是2006年研读《罗章龙回忆录》之后。

中共八七会议会址位于汉口鄱阳街,由邓小平题字。
中共官方和党史界对八七会议的主流看法。可以用新华网关于八七会议的词条做代表:“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陆定一、李维汉都参加过八七会议,后来写回忆录或者接受采访,都回忆过八七会议。这些我要稍后再讲。先说一下八七会议对于邓小平的意义非同一般,是他平生第一次参加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篇文章说:1927年夏,他作为党中央秘书,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第一个来到开会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最后一个离开。这次会议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不同历史时期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

中共八七会议会址内悬挂与会者的照片。
其中有一次,是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来信作了批示,之后周恩来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11月14日,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厅,当看到八七会议会址的照片时,邓小平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向陪同人员介绍起这次会议有关情况。介绍完后,他还对八七会议作了高度评价:“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农民暴动,举行秋收起义,号召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故地重游,重返八七会议会址。此时这里已是纪念馆,一楼举办有辅助陈列,介绍八七会议的背景、经过和意义,二楼尽量恢复开会的原貌,把靠街面的前房布置成会议室。邓小平对工作人员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六天,最后一个走的。”他告诉工作人员,会议可能是在靠后面的房间开的。

晚年的邓小平多次回忆八七会议——他第一次参与的中央级别的会议。
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问他:“怎么样,像不像?”邓小平说:“记不得了,基本上像。”他对会议的记录、会议的翻译、代表的名单、共产国际代表、他当时的身份等问题一一作答,还对何时决定召开这次会议、会议的报告、各地武装起义等问题一一介绍。
八七会议时,罗章龙不在武汉,也无法赶回,沒有出席。但是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篇《中共八月汉口会议》的近万字长文,与中共官方党史的口径有很大不同,持强烈否定的态度。这篇文章在《罗章龙回忆录》中,占了11页,题为“结论”的最后一节,有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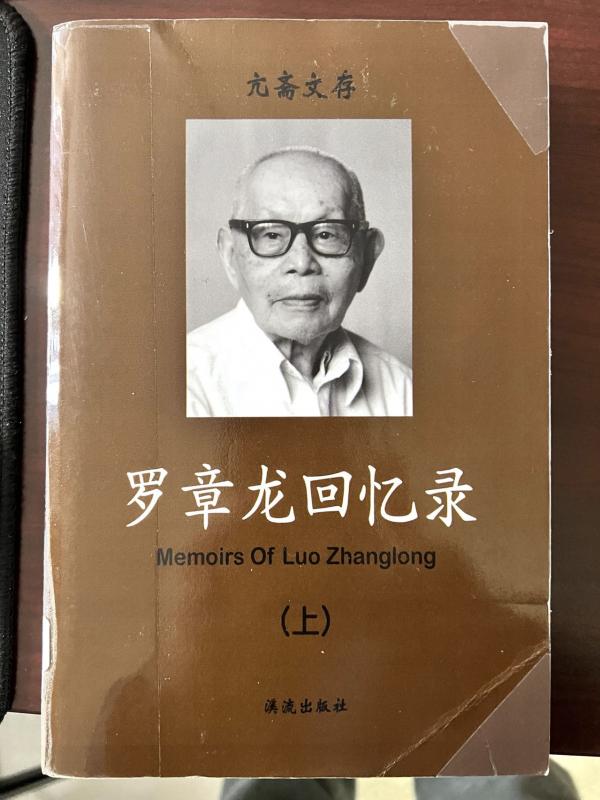
《罗章龙回忆录》书中有万字专文述评八七会议。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1927年是中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国共从合作转向对抗的年份,我尽量简明扼要地交代一下八七会议的背景:4月中旬,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清共,当时国民党的政治重心在武汉,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遵循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坚持不跟共产党翻脸,倒与同党的蒋介石翻脸。中共在这一年5月危急时刻,在武汉举行了五大。然而共产国际新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罗易,不知哪根筋搭错,把一份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机密文电,特地去送给汪精卫看。汪精卫一看文电中指示中共利用国民党、顛覆国民党,取代国民党,五雷轰顶,当机立断与中共一刀两断,就有了“7·15”分共,对苏联顾问和中共人士“礼送出境”:你我理念不同,无法合作,不留你们了,你们爱怎么玩就自个儿怎么玩去。中共随即在半个月后发动八一南昌暴动。八七会议,是在八一南昌暴动之后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人,候补中委3人及其他方面代表共21人。毛泽东参加了。
罗章龙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叙述了1927年八七会议的经过、文件如何产生。当时中共打算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也就是说,中共处在大搬家过程当中,在武汉的中共机构是个临时看守班子。罗章龙说:成立长江局,位于汉口珞珈碑路(现名珞珈山街)。该局所留人员不多,具有看守机关的性质。所以中央工作在半月以内实际上陷于停顿。
国民党紧锣密鼓地要与中共脱钩,中共却忙着搬家,罗章龙在文中写道:“鄂省总工会向忠发席卷公款逃往湖南,刘少奇与瞿秋白等携眷匿居庐山,他们均系自由行动,下落不明。……周佛海首先发表‘脱离赤都武汉’文章,施存统发表‘悲痛的自白’,李达在报上刊登脱离党启事……”这正是人心浮动之际,共产国际却在策划对中共中央采取自上而下的全面改组,换人主掌。罗章龙具体介绍当时的背景说:“……武汉形势恶化,旋即急转直下。1927年6月,国际代表罗易等自中国撤离回到莫斯科,报告武汉异动情况,国际东方部如聆晴天霹雳,一时感到手足失措,乃召集该部全体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为稳定局势起见,确定政治原则,中共继续支持国民党左派……”
罗章龙写道:原先号称国民党左派分子星流云散,所谓“支持国民党左派”实际是“支无可支”。但当时国际指示仍“刻舟求剑”,不知改变。所以南昌暴动时,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起义军队仍树青天白日旗帜,8月1日贺龙自南昌发布宣言,强调总理遗教与拥护三民主义,通观全文纯属国民党口吻,无丝毫工农革命气氛!……

八一南昌暴动虽是中共策划发动,却是用国民党左派名义。
罗章龙说,形势演变,共产国际的政治逻辑终于破产,中共党员已再无人理会,东方部不得不转移了方向,同时为了维持国际威信起见,决定自上而下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撤换书记,另派继任人选,部署既定,乃立即派代表赴中国召集紧急会议。
罗章龙回忆录写道:国际所派遣的代表罗明纳兹、纽曼先来到上海。罗明纳兹是格鲁吉亚人,为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纽曼是德国人,暴动专家。罗章龙图省事,将这二人简称为“二洛”。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搬家,“二洛”没找到中共,就乘轮船溯江西上。七月下旬,国际代表到达武汉,先通过苏联驻武汉领事,找到中共长江局。他们说带来一个方案,主旨在召集一个特别会议,超越五大所选出的中央,另行成立中央。
罗章龙回忆录中写道:当国际代表见到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告以此行任务时,亦农听说甚为诧异,不知所措。答称:“五大中委几乎全部离开武汉,会如何开得成。”对方说:“这样正好,我们决定另立中央,与五大中央无干。”因问瞿秋白何往,亦农说:“也不在武汉,听说到牯岭避难去了,现在住址不明。”国际代表说:“我们立即举行会议,一边设法找他。”由二洛单方决定于8月7日举行紧急会议,由长江局通知有关方面代表到汉口出席。

时任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的罗亦农,后来中共推出了纪念邮票。
由于时间短促,参加会议代表主要为长江局及留汉共青团成员,外省只有湖南、九江代表参加,其它各地因路途较远均无代表参加。罗章龙说:汉口会议由于筹备非常仓促,所以会议时间很短,因此一切文件均在会后补写发出。汉口会议政治报告中主要内容:A.强调大革命高潮中国际路线的正确与中国党领导的错误。B.强调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社会经济的主要内容。C.武装工农,确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地区举行秋收暴动。
据中共党史资料,八七会议对中共领导层推倒重来,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瞿秋白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逼迫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
而罗章龙是这么说的:关于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问题,国际代表提名叫瞿秋白任书记,但阿双(秋白号)仍未露面,通过长江局专派交通员辗转探索,才寻到他的踪迹,随后又派人到九江把他叫回汉口。他到汉口立即被任为临中(临时中央,下同)书记,但他起初表示不愿意干,国际代表坚决叫他干下去。
罗章龙说,出席八月会议代表事先既不知道会议性质,故无从准备,临时又未见到任何系统文件,只凭国际代表所作简单报告,所以也就无法开展讨论。就这样,大家听取报告完毕,就算会议即告完成。汉口会议结束多时,临时中央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及“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几个文件,这些文件均未经会议讨论通过,是事后补写的急就章。

1965年春节,罗章龙与长子罗平海(前左)、长女罗梦平(后右)及外孙女罗星原(后左)。
罗章龙对这个临时中央提出严重指责,他说,临中成立以后,高高在上鲜有作为,当时工农兵革命运动事实上陷于瘫痪状态,与此相应便发生重大渎职问题,造成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与广州暴动的连续失败,牺牲惨重,招致党与革命实力的浩大损失。
他一条条列举说:
南昌军事行动于8月1日爆发,国际代表是7月下旬来到中国的,他亲自知悉此事,汉口会议举行已在南昌暴动后一个星期。就常情判断,对于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国际代表与临中应该密切注视并采取积极措施去争取胜利。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汉口会议并未把南暴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当前这样重大问题竟未加以讨论,或专门研究。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临时中央对于江西方面军事行动,既未发出一项指示,指示作战机宜,又未派出知兵大员随军协助,甚至更未派遣一介使者到前方进行联系,或提供有利于军事的情报,或派人协助解决有关后勤事项。当时临中对此客观上只是隔岸观火,漠不关心。坐令前线几万大军,盲目行军,在失去与后方联系情况之下,进入东江方面敌军预设的袋形阵地,陷于重围。造成全军溃散,几万人缴枪,铸成大错。罗章龙这一条批评,应该说符合历史实际。

油画《秋收暴动》。
罗章龙接着说,湖南秋暴(秋收暴动)原是临中成立时决定的。论理更应十分重视,全力以赴。但临中对此除最初原则上作过一次决议外,以后并未作过具体指示,只是坐待捷报。以致坐失机宜,最后造成平、浏战役先后失利,全局皆非!
至于广州暴动是国际二洛和临中亲自发动的,而且是在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之后举行。论理应接受上两次暴动的经验与教训行事,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在作战计划中对敌我估计不正确,粗心大意,结果又重蹈覆辙。终于是一败涂地,精锐全失,死伤惨重。
罗章龙说:中共所拥武装力量约枪支五万人,加上工农武装为数称足,如运用适当,指挥得人,很有可能克敌制胜,有计划地逐步引导革命走向成功之道路。但最后都一一惨败,他认为临时中央有责任。
我在看中共党史时,有一个疑问:八一南昌暴动与八七会议好像完全是两回事,互不搭界,八一南昌暴动的策划人好像不知道有八七会议这回事,而八七会议的参与者对八一南昌暴动也不加理会。读到罗章龙的回忆录,才明白确实是两拨人、两回事。
罗章龙在文章后半部分,记叙共产国际代表与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后来数年重大决策中的失误。与八七会议没有直接关系,我这里就不说了。
他在结论这一节中写道:
汉口会议——也就是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与中共党史上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会议以前,中共领导革命虽然曲折艰难,但是仍然循照正常轨迹运行。1926年冬乃获建立武汉革命政权。虽然遇到重重阻力与挫折,但从大体趋向观察,政治路线一般没有遭逢到严重的失败。但是自汉口会议起与成立临时中央后,中国革命形势却引起质的变化,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势力乃一蹶不振,由此至1931年第二个临时中央成立。

莫斯科的这栋柳克斯大厦,为中共的太上皇共产国际总部所在地。
为什么会这样?罗章龙说:追源祸始,实与当时临时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息息相关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导演的八月会议(即八七会议),只能说是政客导演的阴谋诡计的一幕。由于汉口会议按其性质是于党章规定以外,鼓动几个人,向中共中央进行夺权,另行成立非法的临时中央,所以也就是中共党内第一次非法分裂党的行动;这种非法行动所采取的形式是不光明磊落的,是封建时代历史上宫廷政变的重演。
罗章龙下面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
中国共产党是与广大革命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党。中共中央的产生与存在是通过全体党员的意志,并由中共成文法(中共党章)所规定的,无论何人都不能用任何藉口,对此妄有所变更;如果野心家不按党章规定而擅自成立中央,篡窃党中央大权,那便是非法行为。这是起码的常识。但东方部却冒天下大不韪,违背中国革命权益,悍然于超越中共权力之上,召开汉口会议,解散合法中央,另立非法中央,并任意指派一个于法无据与众不孚的人作傀儡,代行中央职权。完全违法乱纪不得人心。
罗章龙将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国际也就是第三国际的东方部。他写道:中共是1922年按照规章加入第三国际作为国际一支部的。按照规定国际兄弟党间必须遵守民主精神,彼此平等对待,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与友好相处。但是这次东方部召集汉口会议却违反平等、互助的精神,破坏第三国际章程,践踏国际兄弟党相处准则,横行霸道,违背国际革命道义!自从汉口会议恶例一开,以后变本加厉。1931年东方部再度策划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成立以王明、向忠发、刘少奇等人为仆从的第二个中共临时中央,是再度对中共进行分裂党的组织。其后果严重,毁党与危害革命罪恶昭著,可谓后先一辙!把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地下小朝廷。

八七会议的参加者陆定一,对会议记录和文件的说法与罗章龙不一样。
我要强调,上述罗章龙的叙述和评价,在中共党史上是非主流看法。八七会议参加者的说法,与罗章龙不一样。例如,罗章龙说“代表事先既不知道会议性质,故无从准备,临时又未见到任何系统文件”;又说:“告全党同志书”等几个文件,均未经会议讨论通过,是事后补写的急就章。但参加会议的陆定一、李维汉的说法不同。《八七会议的是非功过》一文中说:八七会议的记录还完整地保存着。有人说,它不是当时记的,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而在事后追记的。陆定一说:“因为事隔多年,我已记不清是谁作的记录,我看了记录后,觉得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是当场记的,不是事后的追记。”李维汉也认为记录是在会场上记的。陆定一还回忆说:“吃完午饭,又继续开会了。下午首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然后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接着讨论《告全党党员书》、《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讲一讲大意和读一读稿子,即交代表表决。……讨论常委报告和文件时,没有发生意见分歧,很快就通过了,然后由常委去作文字修改。”

八七会议的会议室。
陆定一、邓小平和李维汉都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他们回忆会议情况,应该比没参加会议的罗章龙更有可信度。八七会议已成往事,合法不合法的争论也没有了现实意义,不过,罗章龙对当时的背景、对共产国际造成恶果的剖析,乃至对八七会议本身的合法性的质疑,我感觉颇有参考价值,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共许多问题的由来和脉络、理解中共创始者、早期领袖那一辈人面对的复杂的国际国内挑战和他们的思路。